|
|
本帖最后由 半杯凉白开 于 2011-11-30 13:54 编辑
寒冬。
夜色正浓,四周一片死寂。似乎整个世界都沉沉睡去,再也不会醒来。
清晰的狗吠声在这样的时刻突兀地响起,顿时连绵不断。山村的夜晚总是这样静到极致、闹到极致。我就在这样的狗吠声中醒来,看看表是凌晨三点半。想来是邻家的大婶起床了——昨晚说好一起坐船去县城的——我要上学而她去“抽血”。县城离我们这里很远,早起忙完家务再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就到船运码头了。从那里坐船会便宜很多——船是大婶和其它到县城的“人”定期乘坐的,事先谈好了价格。
虽然还有些早,也没什么事情要做,但已经醒来也就很难再睡去。索性起了床来,慢慢腾腾地洗漱完毕也就差不多了。推开门,河风铺面而至,别样的刺骨,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一个人在家也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况且本来时间就不对。天还是黑的,闲来无事,想想还是打了手电筒去大婶家。冬天的路似乎也散发着冰冷的气息,直沁入脚。或许有霜,因为走路会有沙沙地声响。
我推开门,她招呼我坐下,又忙着把家里的一切都安顿下来。农民要出去一次,并不像城里人那样简单。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一个人守着这个家。突然,她蹲下身子,开始用手指挠自己的喉咙。我好奇地看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好一会儿,她转过身子对我说,“昨晚忘记今天要去抽血,吃了猪油的”。我沉默地望着她,不发一言,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终于一切收拾妥当,我们照着手电筒在苍茫夜色中踏上“征程”。寒冬的夜是这样的静,只有我们清晰的脚步声,每一步都在我的心底踏上一个坑。这就是我的乡亲,这就是我的邻家大婶。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来打破这样的沉默,来缓解内心的沉重——我唯有沉默。这时,大婶说话了——是每个人都能预料的说教。说实在的,我讨厌听这样的话语,但我没有反驳。我沉默地倾听,这或许不只是她的期望,还有我那些困苦的父老乡亲们。他们期望改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辈。 这是一个崇尚金钱的社会,而所谓的“献血”是他们能做到的、来钱最快的办法。悲哀?崇敬?是彻骨的寒、是彻骨的痛。
崎岖的山路上汇集着星星点点的灯光,那路的尽头是他们的中转,那路的尽头停靠着“血船”。遇见熟识的同伴,大婶就和他们打着招呼,但并不怎么谈论那个。在他们的眼中,那并不光彩。但迫于生计,队伍却越来越庞大。天微微变亮,依稀可以看见那船了。有人低声地咒骂,“这鬼天气,冷死了”。我在心里附和着,但也暗自庆幸终于要到了。
等前前后后都上了船,天也就亮了,船就开了。船是冷的,风是冷的,心是冷的。白色的客船在古老的汉江上分开两道长长的白色水纹,这水纹持续了十年,也许会有下一个十年。船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有些人始终没有变过,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血农”。600CC的血,随着物价的上涨被赋予不同的价格。或是为了给家人治病,或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是为了修缮破旧的房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贫穷。不,不是他们,是我们——我的那些父老乡亲们。一切都只是为了生存、为了繁衍……
后记:
在那一次经历之后,一直想用自己苍白的文字记下那一段辛酸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我选择了沉默。我的乡亲们已经习惯了每个月两次的“献血”,心里是疼痛的吧?我想,他们如我。有些事,我无力改变,只能接受。
那一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郧阳人民卖血的事情,百度、搜狐、新浪、中国日报网等网络媒体相继发布。一时间,网友众说纷纭。然而真正了解或理解的未必会有几个。或许我说的并不完全确切,但我希望我能用我的笔写下我遥远的父老乡亲,告诉人们一个相对真实的……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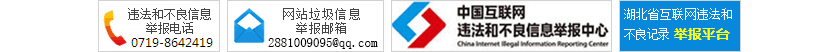
 [复制链接]
[复制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