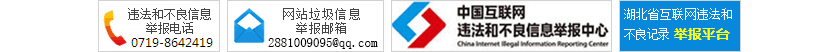|
|
阿夏二十六岁,她是二十六岁那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她的年龄、她的美丽、她最后那一抹笑,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六岁。
午后的阳光从窗子透过来,一束光线缱绻在陈旧的书柜上。那一刻不知为什么,仿佛有一根线牵着我走向书柜,此时,那些多年都未曾动过的书籍,让我心中蓦然升起感动。用手指慢慢地划过它们,就在目光与手指同时停在一本陈旧泛黄的相册上时,阿夏——我不由轻轻地喊了一声,心却深深地疼痛起来。当思念的箭穿越记忆的闸门,那些尘封的往事,那些青春的时光,那些美好而又忧伤的故事,便忽地一下涌出心海……我仿佛听见阿夏在老屋的院子里、在家门前的山坡上、在校园的操场上喊我……
“小菊,小菊。”阿夏站在秋天的院子里喊。我一边高声答应着,一边穿着鞋子。我家与阿夏家紧挨着,两家的院子是用一米多高、粗细不一的木柴棍加成的杖子,拆了杖子就是一家。当我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看到阿夏从她家院子那边,用手把杖子扒出了缝隙,然后从缝隙中伸过一只攥着拳头的小手示意我过去。我知道,阿夏又给我送好吃的了,赶紧跑过去伸出手接着,她反复好几次,温热的花生和栗子,便从她的小手中不断地落在我的手里,不一会儿我上衣的小兜里,便装满了花生和栗子。她从杖子的缝隙中忽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我,嘴角习惯性地向上扬了扬,声音软软而又甜甜地说:“我舅舅来了,给我家拿的栗子和花生,我想这你呢。”紧接着她又说:“我回去了,舅舅还在等我呢。”
我连谢谢都顾上说,便挑着眉毛,深深地吸着从小衣兜里飘出来的炒香气味,用手拍着小衣兜,冲她笑着点点头。她转身一蹦一跳地往屋里走,两条羊角辫在蹦跳中摆动着,衣裤上的小花也跟着跃动起来。我也赶紧回到屋里,先剥开一颗栗子放进嘴里,一边慢慢嚼着,一边又剥开一枚花生放进嘴里,香甜顿时溢满了唇齿间。在吃、穿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那些东西是用钱也不容易买到的呀。长大后每每想起小衣兜里那满满的香甜和温暖,心中便会升起无限的感动。
五六十年代的矿山,家家住的是平房,一排平房有六七户人家,家与家之间的院子,就用木柴加成的杖子隔开。阿夏我们两家住的那排房子开门见山,一条平整出来的五米多宽的过道就在山根下,靠山的一侧有两颗柳树,每当闲暇时,邻里们就会聚到柳树下说话、唠家常,有时候大人们还会在过道,放上一张桌子玩扑克牌,而孩子们则在柳树下或过道上追逐玩耍。
阿夏家四个孩子,她在家里最小,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上面有三个哥哥。那个年代,平日里几乎家家吃不到什么油水,更没有什么零食,家里男孩子多的,粮食就不够吃。阿夏的妈妈是当地农村人,嫁给在矿上工作的阿夏父亲后,一直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全家六口人就靠阿夏父亲挣钱养家,因此,她家的生活比较拮据。她妈妈的娘家住在离矿上不算远的北湾子村,经常有来矿上办事,或卖点自家土产的亲戚到她家坐一坐,吃顿饭再走,遇上来矿里医院看病的乡亲,在她家住上几日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她家的粮食总不够吃,经常把定量供应的细粮与邻居兑换成粗粮。在我的记忆里,她家每天的晚饭一成不变,总是高粱米粥咸菜条,偶尔有个小葱蘸酱或生菜什么的,她的哥哥们都特别满足。
“阿夏妈,听说你家粮食不够吃,用细粮与别人家换粗粮?”妈妈推了推眼镜问道。
“嗯,一到月末粮食就不够吃,所以我就和邻居兑换一些。”阿夏妈不好意思地笑笑回答。
“我家都是女孩,粮食吃不了,粮食本上有不少余粮,以后你就从我家粮食本上买,不要用细粮兑换粗粮了,也让孩子们吃几顿细粮。”妈妈语气诚恳、温和。
“哎呀,那可不行,你家的余粮还可以去农村兑换大米呢。”阿夏妈妈推辞着。
“我家都是女孩,粮食吃不了,我把粮食本给你拿来了,你看看我家的余粮是不是有很多,换大米也用不了这么多,你就放心地买吧。”妈妈真心实意的举动,让阿夏妈妈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辞。
从那以后,阿夏家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用我家粮食本购买粮食,直到后来取消粮食本。我家改善生活的时候,妈妈总会让我把阿夏叫过来,每当那个时候,我和阿夏都特别开心,饭桌上当我俩目光对视时,她会稍稍耸一下肩膀,微微吐一下舌头,用那双纯净的大眼睛,看看左右我的家人,然后低头一笑,那表情可爱极了。
一天傍晚,井下发生了重大事故,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他们接到通知后,一分钟都不敢耽搁,也顾不上安顿我,迅速前往事故现场参加抢救工作。那天,二姐跟随学校的学工学农小组,去附近农村体验生活,两天后才能回来。大姐是知青,在丰宁坝上插队。窗外北风呼呼地吹着,时钟已经指向八点,爸妈还没有回来。我轻轻掀开窗帘看着外面,许是上苍也在为遇难的矿工难过而哭泣吧,一道闪电划破了秋夜的天空,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紧接着又是一道电闪雷鸣,我吓的一下子松开了窗帘,与此同时我听到有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我害怕极了,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紧闭着嘴唇,委屈地想哭却不敢哭,一动也不敢动地缩在屋子的一角。忽然,我想起和阿夏约定的暗号。于是,我到厨房找出擀面杖,冲着把我家与阿夏家隔开的那面墙,有节奏地敲打起来。
这是有一次和大人们看完反特电影后,在回家的路上,天真的我们也约定了呼叫暗号,因为我俩几乎天天见面,所以这个暗号根本用不上,早就让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在我担心阿夏不会记得这个暗号时,竟然听到了墙那边回应我的声音,我倾听着、回应着,兴奋极了,在地上跳了好几下,把深夜一个人在家这事给忘了,好像在和阿夏做着游戏。
不一会儿阿夏跟在她妈妈后面就过来了,一进屋我俩相视吃吃而笑,阿夏妈抚摸着我的头说:“原来你们两个小东西还有暗号,幸亏有这个暗号,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小菊吓出毛病来呀。”
阿夏拉着我的手说:“小菊,今晚你就去我家住吧。”我高兴地使劲点头答应着,跟着阿夏和她妈妈就往外走,走到门口阿夏停住了,返回屋子找了一支笔和一张纸,给我爸妈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们我在她家。
那个夜晚,我和阿夏钻进了一个被窝,我俩相视笑着,感觉特别好玩,她捅我一下,我挠她一下,她给我讲着一个个故事,我便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冬天的一场大雪没过了脚腕子,天地之间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弥漫在天空,只有这个时候,才让人感到城市、矿山和乡村没有距离,更增添了童话的意境。
爸爸一边摆弄着那架新买的海鸥牌照相机,一边让我去叫阿夏,说带我俩去雪地拍照。我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刚要喊,就听见阿夏在我家柴门外叫我,赶紧打开门让她进来。她身穿红色灯芯绒的小棉袄,头戴一顶绒线编织的乳白色帽子,帽子最顶端还系着一个柔软的白色球球,说话时永远都是忽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我们去推雪人、滚雪球吧。”她说。我告诉她爸爸要带我们去拍照,她一听高兴地直拍手,嘟着小嘴说只在照相馆照过相,还是和全家人一起照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照片,更没有在外面照过相。说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愉快的样子真像洁白的小雪花。
爸爸让我们俩尽情在雪地上玩耍,他变换着拍摄角度给我和阿夏拍摄,还时不时喊两嗓子让我们看他。我们堆雪人、滚雪球、互相追逐着,阿夏身上那红色的小棉袄,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像一团火跳跃着,仿佛随时都能把冰雪融化。我们玩得不亦乐乎,忘记照相这码事了。这时,爸爸叫住我们,让我俩背朝山坡,面朝他,互相搭着肩,并说笑一笑,嗯嗯,好,别动了……这时,阿夏忽然看到我的脸粘上了雪,她迅速掏出手绢,一手把着我后脑勺,一手给帮我抹去雪水,就在那一刻爸爸按动了快门,一幅生动可爱、温馨感人的画面,瞬间定格在白雪覆盖的小山,冰雪晶莹的树挂背景上。
那年我七岁,阿夏九岁。
家门前的那座小山,在我看来就是大山伸出来的一根手指头,站在院子里看到的是座小山,可登上山顶时,就会看到远处一片片树林和连绵起伏的山峰。通往大山深处有一条小路,小路两侧的山坡上有农民开垦的荒地,主要种植高粱、玉米和豆子。树木的苍翠和花草的芳香,会从春夏持续到深秋。我和阿夏经常在早晨的时候,坐在山坡上背诵课文,或傍晚的时候坐在山坡上看晚霞,说悄悄话,直到各自的妈妈喊着我们回家,我们才走下山坡。
一天我和阿夏登上了小山的顶峰,趴在那块露出半截身子的大石头上,一边看远处来来往往的行人,近望出出进进的邻居,一边说着漫无边际的话。更多的时候是看我们两家的人在干什么。
“哎哎,小菊你看,我妈和你妈在院子里说话呢,是不是找不到咱俩着急了。”阿夏说话的声音有些幸灾乐祸。
听到阿夏的话,我收回远眺的目光,看到阿夏妈妈和我妈妈隔着杖子在说话,感觉有些着急的样子,我说:“准是找不到咱俩着急了,我们喊她们吧?”阿夏点点头。
我俩站在大石头的后面,露出半个身子,挥动手臂大声地喊:“妈妈……我们在这那。”两位妈妈听到我们的叫喊,同时抬头往山顶上看,又同时招手示意我们下山。下山的路稍稍陡一些,阿夏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我,提醒我注意脚下安全,遇到小滑坡或有石头凸凹的地方,她就会转过身来拉着我的手,帮助我走过去。下山后,她让我站好,然后为我从上到下,拍打着衣裤上附着的尘土。
一个夏季的傍晚,我和阿夏坐在山顶上,看落日余晖轻笼远山,看天边的晚霞,一会儿像燃烧的火焰,一会儿似层叠的彩绸,一会儿又如一幅油画挂在天边。那变幻莫测的图案,让我们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阿夏,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问她。她拉长着声音,说:“嗯,我想当老师,当一名好老师。”
我笑她说:“怪不得你家屋里的门上写满粉笔字,都是你假装当老师写的吧?肯定还学着老师的样子讲课来着,对不对?”
她抿着嘴笑着“嗯嗯”地答应着,一边点着头。然后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
我翻冷着眼皮说:“我想当女兵,女兵多神气呀。”
她用手轻轻推了一下我的头,哼哼地笑着说:“当兵你也是个逃兵。要不然就是让鬼子抓住后,禁不住严刑拷打,然后就招供了,成了人人都想杀的叛徒。”
我大声地说:“我才不会叛徒呢,我在墙上挖个洞,没等鬼子打我,我早就跑没影了。要不然我就像英雄王二小那样,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包围圈。要不就当刘胡兰宁死不屈。”可能是看我说话的表情特别可笑,她无声地笑弯了腰。
我推了她一下说:“笑什么呀,有什么可笑的。”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打逗。还别说,后来阿夏考上了师范学校,真当上了老师。而我与女兵无缘,却当上了一名医生。
那个年代,一根细细长长的皮筋,就能给童年的我们带来极大的欢乐。我跳皮筋的水平,在同院的小朋友中是“高手”,一级接一级地跳,经常把举着皮筋的小朋友累得胳膊酸疼了,我还下不了场。一次,我正和小朋友在家门口玩跳皮筋,外院一个没阿夏高,但比阿夏大两岁,叫桂枝的女孩走过来,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可能是看我跳了好长时间也下不了场,就走上前拽着为我举皮筋的小男孩,说:“表弟,你怎么和她玩呀,我爸说她爸是右派。”
男孩放下举皮筋的手问:“什么是右派,右派是什么?”
桂枝用眼睛斜视着我,说:“右派是黑五类里的。”
男孩更不明白地眨着眼睛问:“什么是黑五类?”
女孩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呀,就是地富反坏右,是坏人”
男孩嘟着小嘴说:“小菊不是坏人。”
一个叫兰兰的女孩,走过来解围地说:“我爸说,小菊的爸爸右派帽子已经摘了。”
桂枝不依不饶地说:“我爸说了,摘帽也是右派,那叫摘帽右派!”
我气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没等桂枝反应过来,上去就挠了她一把。这下可不得了,她像小疯狗一样向我扑来。我来不及躲闪,吓得闭上眼睛,并用胳膊挡住脸。就在这时我听到桂枝尖声地叫喊:“阿夏,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推我?”
我放下胳膊,睁开眼睛看到阿夏站在我前面,用手指着桂枝大声地说:“你凭什么欺负小菊?”
桂枝挑着眉毛,瞪大眼睛说:“管你什么事儿,用你管吗?我就欺负她了怎么着?她爸是坏人!”
“让你胡说八道。”阿夏一改往日温温柔柔的样子,一下子把桂枝推倒在地,并跟上一脚。
桂枝坐在地上,捂着嘴大哭起来,说:“你不就仗着有几个哥哥吗,你欺负人。”
阿夏并不和她争执,而是一手掐腰,蔑视地看着桂枝说:“去年你爸把你妈打的喝了农药,是不是小菊她爸爸把你妈救活的?前几个月你得肺炎,是不是小菊她爸爸给你看的病,开的药方?太没良心了……”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一阵委屈,也不知道为什么,转身就往小山上跑,等阿夏发现的时候,我已经跑到了半山腰。阿夏一边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别跑,一边追上小山。当她登上山顶的时候,我已经躲在高粱地里了。
“小菊,小菊——你在哪里,快出来呀。”听见阿夏焦急地呼喊,我无声地抽泣着,任阿夏怎么喊,就是不想出来。
“小菊,小菊。”阿夏一边喊,一边往山里面走,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怕她走远会出危险,于是我一边喊着阿夏,一边从高粱地里走出来。
阿夏听到我的喊声停住了脚步,转过身站在原地,等看到我时,她顺着山路便向我奔来,我也向她跑去,当我和她只有半米距离的时候,同时停住了脚步,气喘吁吁地看着对方,那一刻,我看见阿夏眼睛里有闪闪的泪光,我仿佛见到了亲人,嘴角往下咧了咧,又抽泣起来。她向前一步,张开双臂一下子抱住了我,带着哭腔说:“小菊,你吓死我了,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
那年我十岁,阿夏十二岁。
阿夏站在午后清幽山谷的花树下,穿一件白色的确良上衣和绿色军裤。头发柔软黑亮,两条越过肩的辫子,用缠绕着淡黄色毛线的皮筋扎着。花树上紫色的花朵层叠绽放,有绒绒细细的粉末花蕊。阳光透过花树的缝隙,衬托着她纯净秀美的脸庞,有细密的汗珠亲吻着她的额头。她用手再次顺着头顶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将挡在额前的一缕头发拢在耳边。说:“这样就行了吗?”
我说:“嗯,可以了,再往前站站,别让树枝挡着你的脸。”
听我这样一说,她往前站了站,顺手拽着伸展过来的枝桠,将它轻轻压住,还像小时候那样向上扬一扬嘴角,下巴收紧,微笑的看着镜头。我稳定好三脚架,调整好相机,冲着阿夏说,别动了,同时按动相机,快步跑到阿夏身边,挽着她的手臂,头歪在她肩上,听到相机自动调焦之后清脆的咔嚓声音。
“别动,再给你单独来一张。”这时,我看到往前又走了一步的阿夏,脸上还带着微微的笑,阳光刚好从侧面给她的脸庞镀上了一层光晕,美极了,我连着按动了快门。后来我到市里照相馆冲洗照片的时候,这张照片被照相馆的工作人员相中了,放大后作为样片摆放在照相馆外面的图窗里。
我们沿着山路行走着,春天的山道,花儿鲜美,草木葱茏。当我们感到有些累的时候,看到不远处一颗大树下,摆放着两块平整的石头,阿夏说:“我们去那里休息一会儿吧。”
于是,我们在那棵树下把军用水壶和背包放在石头上,我和阿夏在树荫下,静静地躺在青草地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望着蓝天和白云,说着梦呓般的话。在我俩的狂想中,所有的一切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设计构思,唯有名字让我俩无可奈何,都嫌自己的名字特俗,不温婉,无内涵,少清新。为此我和阿夏都埋怨过父母,都闹过要改名字的逗乐事,结果名字没改成,反而给哥哥姐姐们增添了笑料。
那时候大陆刚刚开始流行琼瑶,我和阿夏便迷恋上她美轮美奂的故事了,特别是故事里的女孩子,一个个的名字都是那么温婉、可爱、高雅,这让我们心荡神摇,羡慕不已。在我们看来,一个好听的名字,因为能给人听觉上的冲击,所以会给平庸的女孩增添几许亮丽的色彩。
阿夏闭着眼睛说:“小菊,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男孩的名字里要有‘墨’,女孩要有‘蝶’,就是那个蝴蝶的蝶,嗯——再找个姓‘夏’的丈夫。”
说完,阿夏呵呵地笑了。我看着天上浮动的白云说:“我的孩子名字里一定要有‘梦’,或‘幻’。”
那天,我和阿夏说了许多大胆的话,一点也不担心会有人偷听到而耻笑我们。倒是春风有意,好像听到了我们开心的戏语,忽地从山那边飞过来,温暖、萦绕地轻抚着我们的脸颊。躺在青草地上,青草的气息簇拥着我们,心里想的和眼前的景色一样优美。
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学校或是在家里,我们经常会神秘兮兮的相互称呼着“蝶”“梦”什么的。在别人不解的眼神中,我俩相视而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渐渐忘了自己精心挑选的名字,跟着时间一天天长大。
那年我十四岁,阿夏十六岁。
阿夏高中毕业正好赶上1977年高考,为了离家更近一些,好照顾她日渐衰老的父母,也为了能圆她当老师的梦,她只报考了塞外小城的师范学校。可能我和阿夏今生真的缘分不尽,在她上师范的第三年,我也考上了跟她同在一个小城的本科医学院校,而且从我们学校步行到她们学校,也就四十分钟的路程。因为又能经常见面了,这让我们欢喜不已。
一个周日,阿夏约我去她们学校,当我快走到大门的时候,看到阿夏和一个男孩站在校门口。走近他俩,我特意看看那个男孩,足有一米八的个头,阳光帅气,微笑的眼睛清澈透明,看上去非常温厚善良。一件白色的确良上衣,一条深蓝色的裤子,白上衣的袖子没像其他男生那样正正规规地挽到胳膊上,而是就那么随意往上一撸,显得那么自然好看。
阿夏看看我,轻轻地推我一下,说:“看什么看,这是我男朋友,姓夏,叫铁军。”说完冲我诡秘地一笑。难不成是为了在青涩季节里说过的话,当真找个姓夏的?我心里在想。
阿夏又推了推我,我俩心照不宣地一笑,她对铁军说:“这就是我和你说过的小菊,我的发小,伙伴,小妹,朋友,闺蜜……”阿夏说出一大串称呼,把我和铁军都逗乐了。
“你好小菊,阿夏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是你,我真是羡慕嫉妒不敢恨啊。”铁军说话不但落落大方,而且还很风趣。
我发自内心地笑了,说:“我是叫你名字呢,还是叫你姐夫呢?”我这话刚一出口,阿夏使劲掐了我一下,我哎呀一声喊道:“姐夫,你可小心着点,阿夏可喜欢掐人了,你看看是不是都掐青了?”我假装娇滴滴地说。
铁军抿嘴笑着说:“俗话说,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成祸害,阿夏疼爱你。”
“还没怎么着呢,就被护上了,哼。”我抚摸着被阿夏掐疼的地方,笑嘻嘻地接着又说:“姐夫,要不然也让阿夏疼爱你一下?”
阿夏举手又要打我,我躲到铁军的另一侧,说:“姐夫救我。”铁军还是一抿嘴,笑呵呵地说:“中午我请你俩吃饭”
午饭,铁军在食堂特意给我和阿夏打了两份肉菜,看到我俩吃得那么香,他笑了,那笑容是真诚、善意而又舒心的。
送我回学校的路上,阿夏告诉我,铁军是独生子女,父母都是老师,家就住在市里。他俩已经决定毕业后,就在这座小城当一名老师,与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她说第一眼见到铁军,就有一种亲切感,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眼睛,深邃而又清澈,一眼就能望到底,让人心里踏实。她说铁军就是自己青春年少时的梦中情人。
我笑道:“讲讲你们俩的恋爱经过,传授点经验呗。”
阿夏看了我一眼,一笑,然后看着前面的路,眨动着那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着,说:“缘,是缘,就像我和你,都是上苍给安排好的缘。”一路上,我静静地听她娓娓道来与铁军的缘分。
阿夏轻声细语而又滔滔不绝,把她与铁军相爱的前后经过,一下子都告诉了我。快到我们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我们俩都停下了脚步,阿夏有些羞涩又有些自豪地一笑,说:“铁军篮球打得好,人品、人缘都好,有不少女生喜欢他,也有暗暗追求他的女生,但他从不动心,他说,这辈子非我不娶了,呵呵。”看着她幸福和喜悦的笑脸,我也由衷地笑了,伸出胳膊搂着她柔柔的肩,默默地为我一辈子的朋友祝福。
那年我十九岁,阿夏二十一岁。
阿夏和铁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里的同一所中学工作,她实现了童年时就想当一名老师的愿望。我上大四那年的夏天,阿夏和铁军结婚了。我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为他们买了一对可爱的情侣小猪存钱罐,因为阿夏和铁军都属猪。
阿夏高兴地把它放到了写字台上说:“太可爱了,铁军,以后我们把零钱都放在里面,等装满了就存起来,一直存到小菊结婚,到时候我们看看能给她存多少嫁妆钱。”说完她还是习惯性地翘一翘嘴,微笑着看看铁军,又看看我。我假装闭着嘴,眨巴着眼睛,表现出不在意的样子,但内心早已被阿夏这亲情般的语言深深地感动了。
自从阿夏和铁军结婚后,每逢周末我都会去他们的小家改善生活。阿夏每天站在讲台上,一进家就累得倒在沙发上不想起来,铁军特别体谅和心疼她,从不让她下厨房,包揽了每日的三餐。但是到了周末,阿夏总是亲自下厨。夏天,她会做一道拿手的饭——瘦肉茄子馅饺子。我以为茄子就是做菜吃的,怎么还能包饺子呢,等吃了阿夏做的瘦肉茄子馅饺子,才知道茄子还可以这样吃,竟然是如此的鲜香可口。冬天,她会做一道东北有名的家常汤菜——酸菜汆白肉。白肉肥而不腻,菜嫩汤鲜,真是让我百吃不厌。
日子像小河流水,有时溅起愉快的浪花,有时泛起多情的涟漪,偶尔还会滑过一些小忧伤,但更多的时候是平淡无奇。愉快也好,忧伤也罢,我都依然享受着每周那可口的饭菜。
上大五的第一个学期,按照学院的教学计划安排,我和同学们开始到医院转科实习,和医生护士一样三班倒。因为我一直想考研,所以在实习期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下班,就是天天到学院图书馆,查找学习资料,复习考研内容,晚上十二点以前没睡过觉,不知不觉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去阿夏的小家了。一天早上我下夜班回宿舍,远远看到宿舍楼门口有一个徘徊的身影,走近一看是铁军,我感到非常惊讶,想想也就三个多月没见,他看上去老了许多,而且神色黯淡,一脸的疲惫,眼睛红红的。
“铁军,你怎么来了?有事儿?”我有些奇怪地问。并把他拉到离宿舍楼门口稍远的一棵树下。
“小菊,阿夏她……”铁军刚一开口说话,泪水早已溢满了眼眶,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看到他痛苦的表情,我预感阿夏一定出什么事了,焦急地问:“阿夏怎么了?你快说。”这时,铁军无力地靠在树上,伸出手遮住眼睛,却无法阻止泪水从指缝流出。
原来阿夏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前两个月时常感觉肝区隐隐作痛,总是浑身无力,当时她以为是正常的妊娠反应,所以一直没在意,默默地忍受着。最近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些加重,到医院一检查已经是肝癌晚期。看到阿夏每天忍受着痛苦的煎熬,铁军心里生疼生疼的,他劝说阿夏把孩子打掉,尽快去医院治疗。可阿夏坚决不同意,说孩子每天都在她肚子里一动一动,一鼓一鼓的,说那是宝宝在和她交流,怎忍心打掉这可爱的孩子。也就是说,阿夏为了生下这个孩子,已经做好不能接受任何治疗,忍受一切疼痛、煎熬和恐惧的准备。
听了铁军的诉说,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肆意滑落,恨不能马上就见到阿夏。当我出现在阿夏面前的时候,她先是一愣,可能没想到那个时候,我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但是瞬间她就明白了。她平静地微微一笑,招呼我坐到她身边。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轻轻的,轻轻地抱住她,我不敢在她面前掉眼泪,怕引起她的难过和疼痛。这时铁军也走过来,蹲在阿夏面前,把头贴在她的肚子上。
阿夏把我的手也放到她的肚子上说:“小菊,你摸摸,小家伙用小屁股拱我,用小脚蹬我,她在和我说话呢,她一定是怕我不要她,向我讨好撒娇呢。”说完这话,她轻轻地拍拍肚子,又道:“宝贝,别怕,你都能跟妈妈说话了,妈妈可舍不得丢掉你。铁军,你信不信,小家伙能听见我们俩说的话……”孩子在阿夏的肚子里缓慢地动着,就像一根生命之线牵动着阿夏,此时此刻母子连心这个词,用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本来我是来劝她拿掉孩子,尽快全力治病的,可她让我无法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只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控制奔涌而出的泪水。
阿夏抚摸着铁军的头说:“铁军,对不起,我很自私是不是?别怪我啊。”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
“阿夏,我爱你,我爱你!”铁军用发自内心的爱语,默许了阿夏的决定,对于阿夏来说胜过千言万语。那一刻,她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而铁军早已泪流满面。
在待产的几个月里,为了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阿夏连一般的止痛药物都不用。她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恐惧,用超人的勇气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疼痛,在艰难地生下孩子之后,还是那样扬了扬嘴角,带着一抹微笑离开了爱着她的铁军和只看了一眼的女儿。那最后一抹微笑,绽放着她的美丽,闪耀着母爱的光辉。
那年我二十四岁,阿夏二十六岁。
阿夏离去的那一年,我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三年后,我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在办理完大学毕业后的手续之后,我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开往那座小城的火车。
我敲开了阿夏和铁军家的门,铁军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后惊喜地握住了我的手。屋里一切如故,就连阿夏生前摆放东西的位置都没有变,那一对情侣小猪存钱罐还放在写字台上,静默等待阿夏的归来,我的嗓子有些疼,眼睛有些湿润。这时,从卧室探出一个小脑袋,冲着我咯咯地笑。这是阿夏的孩子啊,我走过去一下子将她拥在怀里,就像当年拥抱阿夏一样。铁军对女儿说:“梦蝶,快叫阿姨。”“杰”什么?我没听清,反问铁军。
铁军接过女儿说:“梦蝶,蝴蝶的蝶,梦幻的梦。这是阿夏早已起好的名字。”
这时,小女孩忽闪着和阿夏一样漂亮的大眼睛,用稚嫩的声音,奶声奶气地说:“阿姨,我叫梦蝶,叫夏梦蝶呀。”那玲珑可爱的样子和神情像极了阿夏。
逝去的岁月让这个梦想中的名字,强烈地击打着记忆,那些青涩的白天和夜晚,那十多年前与阿夏躺在草地上说过的话,宛如昨天的光景。铁军的脸上一下子浸出两行热泪,而我却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铁军和他女儿的笑脸重叠在我的眼中……
轻轻地合上相册,有泪流进嘴里,咸咸的……午后的阳光早已变成了金色的夕阳,整个下午我都在心里喊着:阿夏,阿夏。
捧起岁月的水晶,在心海的深处轻轻散落,静听回响,阿夏,你在我心里。
(图来自网络,侵必删)
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123@shiyan.com)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