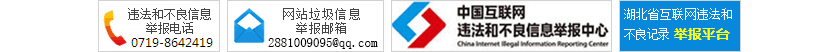|
|
半夏
尽管制作过程不无麻烦,但饺子依旧是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原文明当家的北方人心头最爱,味道也似乎更有合乎方舆逻辑的地道,所以有“好受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话茁壮生存于民间。诚然,饺子身上更多禀赋的北地色彩,当与所谓北人食面南人食米的饮食习俗相关,但食面其实并非北人专美,江南的面食实在更加精致。不过,由于气候水土之于作物品质的影响,在物流远逊于今的古早时代,北方所食面粉的质地和口感,应该更胜于南方,因而面食更流行于北方,或者说北方人更习惯食面。
按照《正字通》里“饺”字条下的解释,它本来是饺饵的俗称。当时的制作程序,是“屑米面和饴为之,干湿小大不一”。而其中的水饺饵,据说就是作诗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唐人段成式所谓的汤中牢丸,又叫作粉角。而北方人读角字如矫,于是成了饺饵,再讹为饺儿。
《正字通》是明朝时流行甚广的字典,后来清朝修《康熙字典》,此书也是重要蓝本,想来它的诠释,该是有权威的。这样看来,所谓饺子,当是角子的变种,应当与形状相关。后世所谓更岁交子,当是傅会。所谓和饴为之,见出那时的饺子可以归入甜食行列。这也不奇怪,叫作饴的糖膏,连较早的字书《说文解字》上都诠释为美味之食,足见甜品在古人饮食谱系中的卓越地位,而主张食药同源的传统医学,也将其定位为上品,可见饴是日常生活中男女老幼都耳熟能详的角色。也唯其如此,甜头也才譬喻诱惑人的好处,甜言蜜语也才可以讨人欢喜乃至哄骗旁人。老话里有含饴弄孙的掌故,其实对甜东西甘之如饴,并非局限于黄口小儿。
汤中牢丸的说法十分具象,见证它是水煮系食品,而所谓的饵,《正字通》说是粉饼,此与粉角乃至屑米面呼应,见证本品食材的稻麦兼具,也即南北通吃,而粉质地的汤中牢丸,令人不由联想到汤圆。至于饼在古代,则是面食的统称。明代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就说:“《杂记》曰: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笼饼是也。疑此出于汉魏之间。”至于饼的涵义,《释名》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所谓溲面就是和面,这是制作面食的基本。当然,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也是覆盖广泛的定义,最简便的标本就是面条。文康在《儿女英雄传》里就提到,今之热汤儿面,即古之汤饼也。所以如今小儿洗三下面,古谓之“汤饼会”。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单有《饼法》,里面记载:“水引,挼如箸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宜以手临铛上,挼令薄如韭叶,逐沸煮。”“馎饨,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饨当是饦的误字。
水引即水引饼,和馎饦都是汤饼旗下的品种,也不妨是其别称。按照贾思勰的记载,水引和馎饦也即汤饼制作时是逐个揉薄下锅煮熟,许多人以为这类同于后世的面片,其实未必不是面条,譬如北方某些地区的扯面抻面,就是此类做法,想来该是最富古意的正宗。在古人眼里,这样的东西,非直光白可爱,亦自滑美殊常,堪称极品。所以晋朝的束皙专写过一篇《饼赋》:“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成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这样的尤物,当然适于担任家庭重大事件的主食,譬如事关血脉延续的生子,所以生儿三日设筵招待亲友,便称作“汤饼筵”或者“汤饼宴”以及“汤饼会”。再沿此思路,过生日吃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诚然,除了充虚解战,汤饼也还有另外的功用。《世说新语》讲故事:“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何晏是著名的美男,面容姣好,尤其肤白,白到令人生疑,譬如皇帝便觉得他是擦了粉。但这样的疑惑不方便用行政命令勘验,也是聪明,皇帝便在炎炎夏日里,赏他一客热汤饼也即文康说的热汤儿面。这恩赐虽然令人感觉有些不合时节,但却是王命,推却不得,吃下去一身大汗则是意料中事。不料何美人的肤白是真货色,汗出如雨后自家揩拭,红衣映衬之下,居然愈发的皎洁。
不要以为魏皇帝夏日赏汤饼是无厘头的颜值测试,晋朝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里便特特提到:“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饼。”而张仲景更言之凿凿的指出:大法,春夏宜发汗。原来皇上貌似的恶搞竟是其来有自,宛然就是习俗,想来当时何美人心中,未必不以为那是皇上的体贴关爱呢。
说起来似乎面条和饺子相距甚远,其实后者不过是加了馅料而已。陆游曾作过一首《岁首书事》,诗云:“中夕祭余分馎饦,黎明人起换钟馗。”他在诗下自注:“乡俗以夜分毕祭享,长幼共饭其余。又岁日必用汤饼,谓之冬馄饨、年馎饦。”和陆游同属宋朝的陈元靓,在其所著《岁时广记》中有《食馄饨》:“《岁时杂记》:京师人家,冬至多食馄饨,故有冬馄饨、年馄饨之说。”如此,汤饼和馄饨扯上了干系,便确凿无疑是馅食了。唐代和尚玄应曾引述《广雅》的说法:“馄饨,饼也。”《广雅》是三国魏人张揖所撰,看来馄饨的名号起始较早。有人以为,西汉扬雄《方言》中的“饼谓之饦”,饦字即饨之讹。历官南北朝入隋作《颜氏家训》的颜之推说: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者也。此话不仅描摹了馄饨的形貌,同时昭示了它的影响力。《正字通》则指出今馄饨即饺饵别名,做法是屑米面为末,空中裹馅,类弹丸形,大小不一。不过提到的食法却是笼蒸。按照专家考证,唐本的《齐民要术》里原有“浑沌饼”,只是今本阙如。唐代成都名医昝殷的《食医心镜》里,则不止一次提及馄饨:丹雄鸡或者白雄鸡一只,如常作臛及馄饨,空心食。丹雄鸡或者黄肥雌鸡一只,如常为臛,作湿馄饨或者面馄饨,空心食之。臛即肉羹。因为版本不一,所以鸡才有雌雄以及丹白黄的或者说法,馄饨也因此有湿或面的可能。有趣的是,这两款药膳模样的鸡肉馄饨方子,居然都是治痢的。
这样的本证材料,足以说明,起码在唐宋时代,水煮面食里,包裹馅料的汤饼,已经成为年节的必备食品,在陆游诗的描述中,它和贴门神并举,俨然是过年习俗的程序性节目。至于馄饨,即便在当下而言,实在就是饺子的同侪兄弟,区别只在馅料的多寡以及外形的各异。甚至前面提及的南人喜食之汤圆,亦是同理,无非馅料和粉面的变化而已,况且南方汤圆的馅料,菜肉鸡油蟹粉什锦,花样百出。按照旧辞书的解释,凡米面食物坎其中实以杂味曰馅。米面杂味,正是馅的关键词,
五代的陶谷在《清异录》里也记载:冬季既大寒,可以停食物,家家多方鸠集羊、豕、牛、鹿、兔、鸽、鱼、鹅百珍之众,预期十日而办造,至正旦日方成,以品目多者为上。用制汤饼盛筵而煎之,名“回汤武库”。大概秦陇盛行。
这样的情景,越千年后依旧,或者说更其成为年中行事的成例。梁实秋的《北平年景》里便说:“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饺子更是必需品,梁实秋写道:“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做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胀。”唐鲁孙也说,北平习俗从正月初一到灯节,家家都是大鱼大肉,如果留客人便饭,十之八九是包饺子吃。印象中饽饽是北方人对馒头之类的称谓,当然也可以指糕点那样的精致面食,《红楼梦》里就有吃饽饽作饭前点补的描写。不过煮饽饽的说法,大概只有太过老北京的前辈才知道了。
再到当下,尤其是北方,饺子甚至成为几乎所有节日的食物,愈发见出其当家的味道。不过,翻检旧籍,除了冬至和正月初一过年,洗三过生日,以及前面提到的六月伏日,七月七日和九月九日也都要食汤饼,《南粤志》则提到,闽人十月一日作京饨,祀祖告冬。原来那时吃的也够频繁,只是那时的食单上未必仅有汤饼,譬如董勋便曾指出,“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北人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也就是说,原本是尝新应季登场的黍糜也即黄米粥才是主题,不料却遭到遗弃,起码在魏时,就已然用汤饼覆盖其余了。如果从善存的角度立论,这当然见证出汤饼或曰面条饺子之类米面食物的可口,足以鸠占鹊巢地替代掉其他作物缔造的品种,哪怕那些其他才是原来的正宫本主。但是这种略略裹挟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优胜劣汰,也让旧有的丰富乃至丰盛,蜕变为去多样性之后的单一寡淡。
其实,就在去今未远的上个世纪前半叶,即便是“从正月初一到灯节,家家都是大鱼大肉,如果留客人便饭,十之八九是包饺子吃”的北平,也并不仅仅盘桓于此。唐鲁孙先生有《春节几样待客的菜点》一文,提到春节款客留宾,自然要准备几样像样的菜点,也就是所谓“年菜”。唐先生倒是没有偏倚,自谦舍下虽然世居北平,可是自从先曾祖宦游南北,家常饮馔,早已食兼南北,味具东西了。他也不过罗列了自家的四样点心、六样小菜,以为大概也就够了。如果有南方朋友,不习惯吃面食,再准备一只暖锅,虽然不是金齑玉脍,但是相对饮啖,也可以宾主尽欢!
唐先生煞费周章开出的这份攸往咸宜、众口同调的年菜菜单是:枣糕,萝卜糕,干菠菜包子,茶叶蛋——这是甜咸点心;炒咸什(南方人叫十香菜),酥鱼,松花炒肉丁,烧素鸡,山鸡炒酱瓜,虾米酱——这是吃饺子下酒的年菜。
这样的规模,听起来和寻常人家的年菜貌似差不许多,甚至单听名目,也算不上多么高大,但其中却潜伏着许多逆料之外。譬如萝卜糕,唐某人自诩,舍间所做萝卜糕,虽然仅和入香肠、腊肉、虾米、香菜,可是选料精纯,软硬适度,就连真正广州大乡里,也觉得是纯正羊城风味。尝遍台北各大酒楼粤式饮茶的萝卜糕,确实不及舍间所制精美。干菠菜包子看似普通,却要早做张罗,每年春季菠菜大市时候,用滚水把菠菜烫过晒干,等吃的时候,用肉汤发开剁碎和入肉末,加入盐、姜、葱、酒做馅儿蒸包子吃,芳而不濡,腴而不腻,自然是点心中的隽品了。茶叶蛋是太过大众的一种极普通吃食,可是要煮得入味,也有其门道的,虽然连壳煮熟,蛋壳要敲得裂而且匀,放入红茶、食盐、八角同煮,茶叶要用未泡过的新茶,煮时水要漫过鸡蛋,也不必加什么猪骨头、花椒等等调味,不过吃一次要煮一次,则蛋白蛋黄可以永远保持鲜嫩。这些制作,虽然寥寥数语,却见巧思,尤其包藏许多耐心功夫和分寸把握,足以见证穿衣吃饭果然要世家才可以备办。
松花炒肉丁倒是稀罕的名目,唐氏也自承,这是舍间常吃的一个菜,在别家似乎还没吃过。皮蛋跟肉都切丁,先用调味料炒肉丁,然后把皮蛋放入同炒,趁热夹马蹄烧饼吃,别有一番风味,吃饭下酒,也很相宜。皮蛋和肉丁配搭,大约非积年浸淫饮食的人家根本想不出的。最刺眼的是虾米酱,一向有上不得台面的重口味声名,然而唐家的虾米酱,要求虾米一定要选泛黄而发红的,虾皮要褪得干干净净,把虾米先用温水洗一下,瘦肉冬笋切丁,瘦肉丁用姜、葱、料酒爆香,再用上黄酱加入虾米同炒。这里黄酱是要紧的选料,习见的甜面酱是要不得的。选料精有时就体现在不要上:这道小菜最忌掺入豆腐干、花生米同炒,如今食肆里大行其道遮蔽味道的辣椒,更是要不得,否则便不成其为虾米酱也。原来一款引车卖浆者流喜啖的下饭菜,竟也能在材料上如此挑剔。
如果拆解字面,年节的年字,本写作秊,下面的千表声,上面的禾则表意,正是年成年景的本意,也即作物收成的赋值,天坛里有祈年殿,祈年就是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农业社会的根本。本土的饮食,实际大多与年节有关,而年节又基本上与农时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林林总总的饮食习俗,实际上都是依托于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时至今日,农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占比日渐萎缩,农时似乎也相应淡出了烟火氤氲的俗世生活,于是诸般花色的食俗只好流连于楼堂馆所里酒局筵席之上的品种,而与家常菜肴缓缓疏离,再加上镇日奔竞的生计节奏,饮食的粗鄙单调其实在所难免。而所谓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潮流,乡绅阶层的消亡,必然导致包括食俗在内的乡俗之流失和蜕变,只好仅存为申遗专家和娱乐型学者口中的侃侃谈资,而其原本禀赋的烟火气息,却遭到抽离,一如隶变让年的字形与年成年景的本意不再关联,一如山气日夕佳的叆叇雾霭变身为野马尘埃的阴霾。
庆幸的是,饺子这枚农业文明下的蛋,依然硕果一般存在于饮食队伍之中,甚至在食味单一寡淡的蜕变中愈发翘楚,即便它的辐射范围更偏爱于中原文明为轴心的北方,但好吃不过饺子之类的茁壮俗话,沉浸其中的终究是整个汉文化体系。当然,关于饺子,类似的俗话不止于此,譬如,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原本是主食的角色,却被不经意间变身为下酒的主菜,而且同时赋予了吉祥讨巧的羡富口彩,足见饺子在人们心目中崇高的百搭地位。这在一个极富传统的美食王国里,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乃至奇迹。
仔细想来,越吃越有,实在就是后面更精彩以及明天会更好等种种理念的大众饮食版,潜伏着无厘头的心理暗示。当然,以饺子作为精神抚慰的口腹地标,也不难确认,该版产生的年代,基本处于短缺经济时代。也唯其所处的时代,饺子身上也就不能不弥漫着白日梦境的狂想,其跃升为百姓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要害元素,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譬如,逢年过节,饺子所担负的,就远不是主食厨房当家花旦所能够限定的。
略有些年纪的人都知道,后来成为白毛女的喜儿的爹杨白劳大叔,在万恶旧社会的某年春节前夕,冒着漫天风雪,从躲债的流浪中,返回家中。丰子恺先生所写《过年》中提及,街上提着灯笼讨债的,络绎不绝,直到天色将晓,还有人提着灯笼急急忙忙跑来跑去。灯笼是千万少不得的。提灯笼,表示还是大年夜,可以讨债;如果不提灯笼,那就是新年,欠债的可以打你几记耳光,要你保他三年顺境,因为大年初一讨债是禁忌的。不过杨大叔归家心切,或许也暗忖不至于晦气到大年夜撞到讨债鬼,虽然他抵家的日子仍处年关。
尽管还债需要银子,但杨大叔回家之前,还是在集市上,用卖豆腐积攒下的梯己,采购了若干菲薄却不乏花色的年货,譬如给女儿的红头绳,以及用于制作饺子的二斤白面——这当然也确凿显示,没有饺子的过年,即便是穷人也不会答应的。由此也奠定了饺子在大型年事活动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分析起来,选择饺子担任年事活动的角色,尽管在后世被分析出若干文化上的繁复寓意,但恐怕经济方面的考量,才是成就它不世声名的根本动因。
饺子的制作材料,虽然杨大叔case中显影了白面,但那只是饺子的外包装而已——当然,可以充任外包装的品种,也还可以退而不得已再求其次,譬如杂面,不过最好是掺和上一定量的白面,否则不利于饺子熟化过程之顺利完成。北方农村在物质匮乏时期倒是有用富于黏性的榆皮面做饺子皮的旧例,也当得水煮,只是口感外相都不敢恭维。
看一位首长的讲话,提到他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首长说他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他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他家强一点,时不时给他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首长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
首长提到的亚麦,遍查不得,猜测应该是燕麦。本土的燕麦以裸燕麦为主,又称莜麦,就起源论它也正是本土原产。从发音上分析,北方俗称的莜麦以及燕麦,都和亚麦切近。
尽管燕麦片是洋人的早餐食品,燕麦粉甚至还是制作西洋糕点的原料,但就本土饮食的地域习惯而言,一等的口粮终究还是小麦粉身之后的白面,所以它才是便于面食尤其是饺子深加工的包裹,这还没有计算其白嫩的视觉效果无疑好过肤色破败的杂面以及其他什么不入流的面。虽说好看的脸蛋换不来大米,但漂亮的面皮,终究能给人带来愉悦哪怕是短暂的愉悦。不用说,白面之能够超越杂面以及其他品流之外诸面,更要紧的是口腔咀嚼之后发生的熨贴口感,说白了,就是好吃。这是食品之于人类最辉煌的感官刺激,自然也是最不待言说的根本要义。
实际上,白嫩包皮之内的填充物也即馅料,才是饺子之成为饺子的关键。今天的大众食堂里,饺子的品种,透露出关键内容的花色,譬如荤素交集的各类蔬菜,家畜家禽的细碎胴体,以及作为重要调料的虾仁,香油,种种。这些当然是饺子的当家内容。不过,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便在举国庆祝的大型年事活动中,由于处身社会阶层的不同,其对具体内容的取舍,也会存在根本上的不同。
譬如,前面提到的虾仁。作为大陆农业文明的后裔,海产品在本土饮食中的意义,天生就拥有鲜亮的舶来味道。所以,虾仁在饺子中的正要,原本是提拔味觉的调料。不过,当食用饺子的主家之经济状况,足以达到富足的情况下——譬如杨大叔的债主黄财东,便可以由其担当主料,其中透露的,除了口腹欲求的放纵,更是一种对稀缺物质的夸张铺排。
但作为小康之家的主妇,便不可以如此奢侈,甚至家畜家禽的胴体与荤素蔬菜的配搭,也会在性价比的考量后,拿捏适度,如此,方显出持家的手段。所谓下得厨房,除了做得出,更要做得巧。
至于杨大叔家的饺子,起码在他老汉负债期间,过年之外,大约是不大方便享用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即便是还债间隙,以重大年事活动的名义,私下里改善生活,作为穷人家闺女的喜儿,操办的饺子之馅料,不必说,其中除了虾仁不可以作想之外,甚至家畜家禽的胴体,哪怕是局部散碎胴体所能启动的腥膻肉味,也是不会有的。大树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公母俩经营的人肉馅料,虽然据江湖人士认定口感绝佳,且又是无本买卖,但作为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底层守法农人,哪里有胆问津。
杨大叔也早已坦承,年货中食品类,只称回了二斤面,其他的再没提起,也不必提起。这种不在话下,自然基本上对包皮之内的填充物,做出了不二的选择,估计也就是北方冬季最当家的白菜了。白菜固然是好东西,但缺乏了油水调料,白菜作馅的饺子,便只适合称作东西,而未必是好了。
当然,穷人的年节毕竟也是年节,而且贫穷绝对不影响人民群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譬如荤腥,其实未必完全缺位。依据古人对荤之指认,但凡气味扑鼻的食用植物,都足以跻身荤之行列,譬如葱,蒜,茴香,韭菜,姜。所以过去说出家人戒荤菜,绝对不是不准吃肉的意思。肉自然是不可以吃的——富有禅宗意味的新派解读除外——但那另有戒条明示,所谓戒荤,无非是不让师父师太们吃那些气味刺激的东东。至于不让的理由,以非出家人的立场揣摩,大约在保障清净道场空气质量之余,更要紧的是,这些违禁品容易给出家人的身体内部带来某些不合出家人其他戒条的欲望吧。至于荤腥不再细分而一体专门落实在肉类身上,则是后来十分晚近的事。
按照上述拆解,譬如喜儿妹子的饺子馅里,作为所谓荤的代表,韭菜茴香之类自当阙如,因为那时还没有淆乱季节的大棚,只好是罕物,倒是便于贮存的葱姜,才有机会按照适当比例,介入其中。不过,无法改变的是,以动物胴体为标志的腥,则依然是经济能力限制下的绝品,即便是富贵人家熬取大油剩余下的油渣,实在也是难得觅及的罕物。这是硬道理,不是玩弄几个文字游戏就可以胡乱变换的。当然,北方农村一向有用油条充当饺子馅料腥物的传统,虽然主材无疑是面食,但通体还是浸透了高温铺就的油水,拥有熨帖的替代性口感。
此之外的其次,则是粉条。粉条入馅的思路,推测起来,应该是利用其Q软的属性,以价格低廉的纯植物性产品,充当了山寨版的动物胴体。这自然是连油渣油条都难以踅摸的短缺经济时代,穷人智慧的结晶。贫瘠的土地上,照样可以盛开花朵。至于花朵的实际品相,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而以舶来品身份赢得饮膳正要的虾仁,鉴于经济取舍的门槛,不论作为主料还是调料,在老杨家更加无从谈起,甚至其孑遗的皮毛——虾皮,也根本不存在获得的可能。不过,虾仁所充任的提拔鲜亮之功能,倒也未必会因为它的缺位而流失。百姓眼里如同甘草和合百药一样拥有万能调味品称号的盐巴,尽管在酸苦甘辛咸的五味之中,被排挤为末席,然其所具备的调鲜作用,却也并不因为席位的边缘而有所减色。所以,早有方家如陶弘景深刻指出,五味之中,惟此不可缺。大约正是因此,盐巴在古代,一向肩负着上供国课下济民用的重大职责。由此倒也不妨将排序上的末位,理解为大轴在后的意思。
诚然,在提拔鲜亮的问题上,盐巴之与虾仁两者所唤起的味觉冲动,绝对不在一个量级线上,其间的差距,甚至以天壤云泥形容亦不为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紧俏的虾仁扩展铺张为包馅主料所实现的欲求放纵,且成为暴发户或曰土豪们的心头最爱,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不论饺子在当初食品行业的设计初衷如何,其所达到的实际效果则是,任你是家财万贯的大富之家,还是境遇殷实的小康之家,甚至如杨大叔喜儿父女这样生计窘迫的贫寒之家,汤锅里熟化之后捞出来的,都是一派粉嘟嘟的热烈景象。在用嘴巴实施最后考评之前,所有内容填充物之间的差等,都被那层厚薄适中的包皮,宛如一床锦被,统统遮盖起来,分明是天下大同的和谐氛围,完全屏弃了杀富济贫的暴烈,而大有传统淑女一般温柔敦厚的古典韵味,营造出一种不容言说的吊诡平等。无论富豪穷汉,在这层具有屏蔽作用的外观遮盖下,都获得了不同量级的心理抚慰和诉求满足。这就无怪乎饺子成为再恰当不过的年夜饭主角。
更有意味的是,当那层锦被一般的包皮被咬破之后,各色馅料对于各色人等味蕾所给予的感受,尽管在生理味觉方面达成层级不同的差异刺激,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其在精神味觉方面所营造的效果,居然都会被类似的所谓幸福满足蒸腾氤氲着,颇有快刀斩麻般的统一划齐,将其称之为终极感受,应该是不会引发什么争议的。
一向有人说,富豪的幸福感未必及得上乞丐。这话听起来无疑犀利,颇有将豪绅打翻在地却不屑于瓜分浮财的痛快,但也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狐狸葡萄的著名博弈。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实在于不经意间对财富流露出某种略显阴暗的心态,相比起饺子所达成的不论财富占有份额的多寡,而各自获得各自愉快的双赢,之间的跳差,真的不可以道里计也。
但凡什么领域,一旦抵达某种具有超越性的境界,主流话语体系总习惯将之譬喻为艺术。若此则完全可以将饺子看作是一道意境超逸的装置艺术,而吃饺子也从而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寓意丰富的行为艺术。当然,该艺术是绝对现实主义版本的,却又不妨是超现实主义的,因为不论男女老幼高低贵贱,对该装置及其行为,都会有自己会心的阐释,其具体意图的究竟若何,答案就善存在每一个执著于饺子的人们心底。
如此不可思议的多重契合,使得饺子终究成为民族食品经济学中大师级的作品,其所裹挟的繁复意象,披靡纵横,无可替代。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
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123@shiyan.com)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