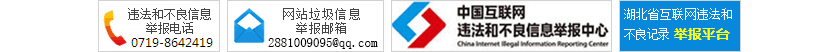|
|
小珍她妈人称“拐儿”,真名实姓无法考证。她年幼丧父,家境贫寒,赶到出嫁的年头,也是小珍爸的福气。那年月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既没三茶六礼,也没操办筵席。经人那么一撮合,便把拐儿领进了家门。在湾子里“拐儿”的绰号也就嚷开了。
回村路上,稀稀拉拉地走着田里干活回来的人,特别是女人,明知家里猪在嚎,小娃在闹,灶堂该点火了,所以步子也快些。
拐儿肩上一根扁担,两头大包小包的“吱呀,吱呀”挑着今天摘回的棉花往家赶。拐儿虽说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从那挑担稳重的脚步中也能看出有一股俊巧、干练的灵气。
踏进家门,放下担子。
“小珍,你爸搞么家去哒?”
“不是和您郎一起捡花吗?”端着米盆准备淘米的小珍说。
“冇呀,我等他帮我挑花,到现在还冇看到人影子。”
小珍放下米盆:“妈,您也该管管爸爸了,人家喜子哥的梨树快结梨了,我们的还是不到一人高的梨苗。刚收回的两千斤谷了也让他卖了,小弟的上学报名费还是找二叔借的,定是到哪个屋的打麻将去哒!”
拐儿由于娘家寒薄,对丈夫总是逆来顺受。白天干闷活,晚上被丈夫勒在怀里闻汗臭味。好在前些年计划生育对他们威胁不大,一连生了三个孩子,眼看大女儿已成人,又长得水灵,看得出,不少媒婆子盯着小珍两眼贼溜溜转。要用钱的时候到了。小儿和小女儿上学也要钱。往后的艰难日子还长着呢!拐儿思忖着如今孩子们大了,他也不敢再对自已蛮横施威了,要拿出滴狠劲跟他斗斗。
拐儿出门问了几家乡邻,都说没看到,经过召喜门前时迎面碰见召喜正担猪粪去菜园。
“喜子,碰见你杨大叔了吗?”
“大叔呀,没准在巧儿嫂那里。”
拐儿转身朝湾子西头巧儿家走去,召喜挑着粪担惊讶地望着拐儿那气鼓鼓的反常神态。
拐儿一溜跑到巧儿家就听见里面吆五喝六、自摸开和的叫唤声,踏进房门口,对面正坐着巧儿,边座上是小珍爸。拐儿怒声道:“我娘母子在地里累死累活,你好闲心!良心让狗吃了啊!”小珍爸侧过头来一时搞懵了,老婆今天呛哪搞的?定是吃豹子胆了,旁边两个人见不对劲,立即合牌随身说:“时间不早了,也该回了。”
滿头狮子发的巧儿下嘴唇包住上嘴唇地衔着一支“金芙蓉”,一缕青烟徐徐地薰向那白里泛黄的面夹,两只布满血丝的斜角眼不住地眨巴着,然后用左手食指与中指夹下那烟卷,嗲声嗲气地说:“哟……,大男人让锅边转的给镇住啦!我今天手气好,这盘又要和,不来就开,开!开!不开不让走!”
小珍爸外号“大洋马”,体格粗壮,腿长胳膊长,浑身是力气,干农活该是个好把式。前几年搞包干制,有人包鱼塘,垦荒湖,闹副业跑生意,各显神通。“大洋马”什么也干不好,什么也不想干,就会捣弄那地里的几样庄稼,没文化,又不接受新的科学种田方法。还是去年,把一瓶“二甲四六”农药拿去治棉蛉虫,活生生地毁了一亩多棉田。眼看人们生活都富裕了,有的盖洋楼,买彩电,穿洋服。有的成天吃喝玩乐,逛市场,没黑没日地打麻将牌,“大洋马”看着眼红,他觉得自已并不比别人憨,于是他选择了打牌消遣。打牌要钱,他胡弄着拐儿把刚收回的两千斤谷子卖掉,理由是现在是市场经济时期,粮食放在屋的白放着,不如投放到市场上去。可是那牌艺又不精,没几天工夫那两千斤谷钱已存不过半数,今天拿去的两百元钱都进了巧儿的裤腰兜兜里。
一脸霉气的大洋马象只斗败的鸡公,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到厨屋的吃了点冷饭,然后用湿毛巾擦了几下脚就进房去睡。这时孩子们都已睡下,他揭开床帐,只见拐儿左右一滚,把被子裹个严严实实,就如那蚌壳见了人---没缝。大洋马欲去拉被,拐儿伸出头来说:“你回来搞么家?到外头睡去!”大洋马本来没好气,在巧儿家里当人多面没发作,此刻立即怒吼起来:“么样?你要讨打!”
“你打吧,打死了这辈子也免得受罪了!”
“好吧,那你就受着!”大洋马脱下布鞋,扬起来准备朝拐儿头上拍去,突然脑子一个念头闪过。那还是小珍刚满周岁的时候,把拐儿打了个折脚跛手,鼻青脸肿。第二天拐儿突然失踪,害得自已在外边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有找到拐儿,自已又顾孩子又顾地里的庄稼,急死人了,还是好心的乡亲们在外踫上拐儿说死说活给劝回来的。想到这,他的手不知不觉已放下。朝后房一看,女儿这么大了,再闹起来让孩子们难堪,更惭愧的是女儿已成人,还住在自已一间房内,所谓的后房只是前面的床铺跟后面的床铺用一块布帘隔开的。只怪自已没本事,不能盖大房子,想到这不由得软了下来,只得低声叫唤着。
“拐儿,拐儿,让我上床吧。”
没有回声。
“拐儿,拐儿,让我……。”
夜深了,只听得拐儿那匀细的鼻鼾声。
隐隐约约还可听见:
“拐儿,拐儿,让我......”
(待续)
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123@shiyan.com)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