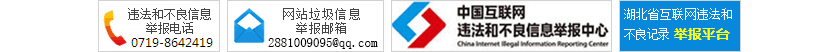|
|
惊人院是什么?
全球唯一的非正常故事研究中心,脑洞、悬疑、热点、现实,各种题材小说故事带你进入现实裂缝,获取超乎想象的研究成果。
我最近收到了好哥们大三儿孩子的满月酒邀请,让我不禁想起许多被刻意遗忘的往事。世间职业千千万,或许很少有人听过“屠小”这个行当,今天,我便将有关它的故事整理成案。一切要从认识久哥说起······
第一次见久哥是在去年的深秋,因为大三儿。
大三儿是我高中同学,宿舍上下铺,穿过一条裤子的兄弟,胆小懦弱,不抗事儿,遇上问题每次都得找我帮衬和解决。这样的人,反倒娶了个漂亮老婆小凡。婚后没多久,他便打电话给我说他老婆怀上了,约定孩子生下后无论男女都要认我做干爹。
九个月后,大三儿突然找上我,沉闷着脸说要让我陪他办件事儿,神神秘秘,一路上啥线索都没问出来,车子拐进医院,我更困惑了,他继续沉默不语。
跟着他来到妇产科,我问,嫂子生了?
他低下脑袋摇头又点头,领着我走进婴儿室,没走两步,他掀开身旁的罩子,保温箱里的孩子奄奄一息,我这才恍然大悟,问他孩子这是怎么了?他叹口气说是残障婴,我相当吃惊,下意识说出能不能治,他看了我一眼,露出悲痛的眼神。我说,那怎么办?他摸了摸玻璃罩说,给孩子办出院手续吧!
这下我更震惊,我拦住他问,是缺钱吗?我是孩子干爹!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就得了!你这样办出院手续,不就是让孩子等死吗?这事儿嫂子知道吗?
他挣扎开,双手拍着大腿说,先天性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想治吗?
我苦口婆心地劝说,北上广的名医名院都被我拿出来比较了个遍,他还是意志坚定地走进了挂号厅。
交给护士手续的时候,大三儿的手有些颤抖,眼里布满血丝,自觉做了错事,护士接过单子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屋儿里人都做好决定了吧?
大三儿点点头说,做好了。
护士指了指走廊拐角的楼梯说,那你抱着孩子下楼去后院找久哥,他一般就在车库斗地主。
到现在我依旧没有搞明白大三儿究竟想做什么?云里雾里地就把孩子抱出来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车库,果真有三个人裹着军大衣抽着烟在斗地主,大三儿走到个子颇高体型较瘦的男子面前打招呼。
他就是久哥,头发不算长,但看得出是自然卷,久哥先是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大三儿掏出的单据,抿口烟说,你这个情况得两千。
大三儿连连点头说了三个好。
久哥指了指我问,这人是谁?
大三儿说,我弟弟。
久哥挂着疑惑地“哦”了一声,跑进车库中央,不一会儿,开出辆白色的五菱宏光让我两上车,路上我几次小声问大三儿这是去哪里?为什么不先把孩子带回家?毕竟这路走得越来越窄,我生怕他做出什么错事,但他就是不回答问题。
面包车最终在一座小厂房停下,久哥锁好车门,打开厂房门,一股冷气扑面而来,以为进去会看到一条条挂着得生猪肉,却发现室内很空旷,存放着的都是些蔬菜,走到顶,久哥打开个小门,密闭空间,大概二十平,立着几台冰柜,他打开其中一台看向大三儿说,把孩子给我吧,放心,刚消过毒。
我皱起眉头刚准备开口,大三儿狠狠地抓了下我胳膊,先是把孩子递给久哥,接着将自己连同我推出门外,后脚刚着地我就往里冲,大三儿挡在身前说,别冲了,这是我同意的。
我看着大三儿,指着小门说,三儿,你们这是杀人!
大三儿跺跺脚说,是!但又有什么办法?把孩子抱回家?然后让小凡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变得虚弱直到死掉,这事已经给小凡带来很大的心理创伤了,要是让小凡亲眼看到孩子死,说不定她会做出什么事儿?
我说,那你可以继续放在医院啊!
大三儿哼了一声说,医院?放在医院没有办法治,那些医生就是一早一晚在婴儿室溜达一圈一天收我几百块钱,凭什么?像是这种事儿,很多残障婴儿的父母都做了,我有什么做不得!我有什么做不得!
我说,你今天喊我来就是让我陪你杀孩子吗?
大三儿瘫坐在地,抱头痛哭着说,哥!我没有办法!我害怕!孩子刚生下来哭都不会哭,医生跟我说这娃得了病,即使治也得去医疗技术好的医院做手术,而且成活率极低,便是成功了,将来也不能和正常孩子一样长大,我没得办法,我不想孩子刚出世就得动刀子,就算侥幸可以存活,那也是活受罪,再大点还会遭人冷眼和歧视,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孩子好!
久哥听见吵声,走了出来,拉高衣领说,几分钟就好了,这里有小棺材,等会儿把孩子抱出来就简单埋了吧。
我将矛头指向久哥说,你做这种生意违法!是杀人!要判刑的!
久哥笑了笑说,孩子是你们从医院抱来的,我是开车的,要说杀人,我们都是共犯,都该被抓起来,这位老弟别急,孩子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你们家人下不去手,那只能我们代劳了,还有啊,我们只是用简单的方法把事情解决,让孩子躺在冰柜里安详去世,这样全家都轻松。
事已至此,已无挽救余地,回来的途中,大三儿一直说拖累了我,我没搭理他,但发誓这事儿是肯定要烂在肚子里的。
半个月前,我在北京出差,大三儿打来电话报喜讯说他们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七斤六两,是个姑娘,笑起来甜甜的,长得很像小凡,结束工作回来第一时间我就跑到他家道喜,一大家子添了新丁,其乐融融,看来已然忘记了那个孩子。
但我记得,也唤起了我对久哥的记忆。我没问大三儿,而是去了那家医院,在车库口等了两天,没等到,只好厚着脸皮问车库的保安大爷,这才得知久哥夏天出了交通事故,两条腿粉碎性骨折,正在家养骨头。
作为撰稿人,我想采访他,便和大爷要了地址,特别豪华的一地方,在珏城的果子渠,唯一旧村改造修得是别墅的村子,除此之外还有座大教堂,本以为走要很远的路,才发现离我住得地方挺近,开车十分钟左右,跟着地址找到门牌号,按了铃,几分钟后有个姿色不错的女人开了门,这是久哥娶得第二任老婆。
我说和久哥是朋友,一直在外地,刚回来不久,听闻久哥身体抱恙来看看他,轻而易举就被请了进来,久哥正穿着睡衣半躺在沙发看球赛,腿上盖着块毛毯,他只看我了一眼,指着我说,我知道你小子,那个说我是杀人犯的后生!
很意外,受宠若惊,我只好坐在旁边哈腰点头斟字酌句地说清来意,久哥理解力不算强,喝完整杯茶才说,那你有什么想问得就问吧,没想到你还是个作家,怪不得当初那么愤世嫉俗,但是你要是写文章不准用老子真名!老子还有漂亮媳妇儿要养!
我当然表示赞同。
久哥是在09年接触这个行当的,帮着那些生了病娃儿残娃儿却又无力治疗和抚养的父母解决问题,说白了就是帮他们杀死自己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在当今社会,别说残障婴,就连正常健康的儿童部分家庭都养不起,有些父母狠下心,把孩子带回家,枕头一捂,棘手的事儿就了啦,但大多数父母是下不去手的,那便只好找“屠小”代劳。
“屠小”是当地方言,顾名思义,就是宰小孩的意思。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珏城。
当时珏城农村生下很多体智残缺的孩子,这些孩子被村里老一辈说成是邪胎,得消灭,但家里人自个了断不妥,弄不好一家人都会染上霉运,神婆神道们发现这是个商机,纷纷宣扬自己可以清理邪物附身的孩子,慢慢地就有人找上门,每当村子里出现这些神婆神道走进村子,村民就会说,屠小来了,屠小来了,这才有了“屠小”一说。
随着改革开放,科技进步,发现当时那些所谓体质残障的孩子大部分只是一些小毛病,医院完全可以进行治疗,多数人也开始相信医院,不信仰鬼神,屠小这个活儿渐渐消失。
可惜时代发展太快,资源过度开发,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每个人都成了亚健康,尤其伴随着经济发展迅速的八九零后,所以久哥说自己从09年开始做屠小,不是没有道理。
八十年代生人陆陆续续在08年开始结婚,成家意味着生子,那时候大家对婚前身体检查这个概念还很模糊,结果便是每月都有那么十几胎残障婴儿。
久哥不是医生,初中毕业就被父母送去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在本地医院妇产科当一名护工,每天就是帮着护士照料那些新生儿。
他清晰地记得,那是八月份的下午,天气热得不像话,七八个父母堵在主任门口提出抗议,说凭什么就得让我家孩子出院,主任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些父母见自己的孩子不健全,就不想治,也不想带回家,想让孩子在医院里等死,免得日后成为累赘,可是医院哪允许这样,可又闹得凶,他没得办法,只能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个文质彬彬的老头,这是久哥的师傅,叫老傅。
老傅笑容满面地和那些父母交涉半个小时后,父母们都不闹了,纷纷办了出院手续抱着孩子在主任办公室等老傅。
久哥也不清楚自己是命好还是命差,偏偏在主任和老傅出来的时候,三个撞了照面,主任看着久哥冲他一笑,问他想不想挣外快,他没犹豫说想,因为那时候他正追一个姑娘,想给对方换台新手机,
久哥就和抱着孩子的父母跟着老傅去了市郊区的一家小门诊,老傅先是给六个父母打了条子告诫他们明天再来,剩下四个父母就把孩子抱给了老傅,老傅抱起两孩子问久哥会不会打针,久哥点点头,便依着老傅吩咐把另外两孩子抱进了里间,给孩子打针的时候久哥问老傅打得是什么,老傅说是安定,把久哥吓得一屁股就瘫在了地上。
他亲眼看到孩子们失去呼吸,依次被老傅放进小棺材里,给送了出去。事后老傅给了他五百块,又请他喝了顿酒,他这才了解到屠小这个行当。虽然看似做得是违法的事,但没人会告发,父母们还会说你是在解决难题做好事,关键是挺赚钱,当时一个孩子的价格是五百块。
我问他,这些孩子被那个后一般被父母送去了哪里?久哥说,刚开始我们不负责善后,有找山沟埋得,有送火葬场的,还有往棺材扔俩石头丢河里湖里的,不过后来被那些父母口头投诉,只好在西郊的山头包了块地,把孩子火葬后,再埋在土里。
老傅带了久哥两年,便癌症病发去世,这摊子久哥顺理成章地接下。13年,珏城因为出现医闹事故,卫生局大盘查,查处了很多违禁药品和医药贩子,久哥的行当多多少少和医疗扯上点关系,搞不到安定剂,生意一度紧张。
他觉得注射安定这种办法行不下去,得另辟蹊径,走了不少关系,跑了趟上海,发现那边的屠小规模比他要大得多,人家早已不用药物这种低级的方式清理残障婴儿,而是使用冷冻——将婴儿放进零下二十度的冰柜,也就十来分钟。
但我觉得这俩办法都挺违背人道主义,久哥见我神情轻蔑,又说这事在外国也有,那些国家的办法残忍多了,把婴儿放在密闭的空间,往里喷一氧化碳,要不就是直接注射可卡因,他们才是真得杀孩子,而他只是在帮助这些苦难的孩子尽早升天。
我说根本没有天堂。久哥橘子剥到一半,停下手说,可是这些孩子如果无法治疗,活下来,对他自己和家人来说,生活就成了地狱。
我说现在医疗技术发展这么好,很多婴儿是完全得以治疗的吧?他说我把世界想得太过美好。
八零年代生人现在慢慢步入壮年,目标客户早已变成九零后,他说,这些九零后虽然看似在温室长大,从小受到保护,可这生态环境越来越差,谁又能确定他们就一定是健健康康的长大,如今这时代,吃穿住行都是那么的不安全,哪年不出几个怪病,更别提这些呱呱坠地的婴儿了,所以生意不仅没有低迷,而是越来越火热。
他把剥开的橘子一分为二,给了我一半说,我这一年大概要接一百个活儿,可怕的很。
我问他,你们做这种事儿晚上能睡得着觉吗?不怕遭到报应吗?他先是说我迷信,紧接着叹了叹气,说起他两个伙伴。
早些年,秋宝和他一起拜师,年纪轻轻,不怕天不怕地,上手比久哥快,老傅特别看重他。
可随着时间推移,秋宝精神就受不住了,每天念叨自己不干了不干了,做这种事情折寿,其实一切都挺顺利,只是因为某一次秋宝打安定,一针下去,孩子非但没睡,还哭得更凶,老傅见状,连忙拿起被子捂在孩子身上,就那么捂着,直到哭声停止。
之后,他每天晚上都会梦到一个孩子被捂在被子里哭,这一哭就是小半年,秋宝干脆停了活儿,转行做了出租车司机,每周跑到白马寺烧香拜佛,总算不再做梦。
过了几年,秋宝找到久哥说自己欠下赌债,不还他们就要打断腿,想要重新干“屠小”,久哥觉得好歹都是同门师兄弟,便答应下来,还和他说现在不打安定了,是冷冻,秋宝一听面露喜色,这次把婴儿往冰柜一关总不会再出现动静吧。
可惜刚干半个月,秋宝又不正常了,说是老能听见冰柜里有婴儿哭声,而且那冰柜还是空得。久哥看不下去,帮他还了债,让他回家做点小生意,别碰这个了,此事作罢。
几个月后,久哥正巧路过秋宝住的小区,便去拜访,结果秋宝老婆说秋宝患上了被害妄想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至今还在里面关着。
另一个是久哥的徒弟,叫阿桂。我皱皱眉头问他这个行当还有女人做?他说不是,这小子其实叫阿鬼,但鬼这个字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吉利,便改叫成了阿桂。
阿桂是个挺聪明的小伙子,抗压能力也强,不过爱喝酒。
有天晚上,从练歌房出来,酒兴正浓,便去洗浴中心,一晚上睡了四个姑娘,硬是把自己折腾死了。
久哥觉得事出蹊跷,便差人打听,得知阿桂是精尽而亡,他跑到洗浴中心问了那四个姑娘,姑娘们说那晚阿桂特别猛,像是变了个人,说什么要报复。
这人死了,就得办丧事,请了好几个阴阳先生,都不愿接这活儿,说这个年轻人惹了一群小东西,得找高僧超度。
说到后来,这事越来越玄乎,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我就没怎么记,总感觉久哥在撒谎,但他在说阿桂的时候,眼角确实有几丝湿润。
我心生巧思,转变话题,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父母选择放弃自己亲生的孩子,久哥说委托人一般都是男方,家里一看生了个残娃儿,就瞒着女方把事办了,事后再告知,先斩后奏,一切已成定局,女方知道无法挽回,也就是闹个几天;也有把事办劈了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离婚,谁也不会去追究责任,毕竟做这事情也是经过双方父母同意的。
久哥又说,其实很多父亲在得知自家孩子是残障儿后第一时间也是想着怎么治,但很多时候,因为各方各面的原因,这病很难治成,他曾经亲眼见一个父亲站在婴儿房外打了一下午电话借医疗费,直到关机没借到一分,蹲在地上抱头痛哭,有的父亲甚至知道结果后,就从来没看过孩子一眼,怕有了感情。
他也遇到过不少得知自己痛失亲子的年轻姑娘来找他,跟他要孩子的命。也是苦,只当了几天的妈,被家人蒙在鼓里,自己孩子便没了,这些姑娘也不能拿她们怎么样,只好给她们家人打电话跑来劝说,导致久哥周围经常性的是整家人抱在一块哭。
久哥叹口气,念叨着说,其实找他来冷冻孩子的几乎全是普通家庭,经济拮据,再遇上人情淡薄,孩子还救个啥,残障儿诞生的事情本就绝望,倒不如绝望到底,还能有点希望。
我突然想起悖论中有一个电车难题,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可这些孩子连牺牲的意识都没有,毕竟刚出生,就得让他为全家付出生命,突然感觉这些孩子很伟大,伟大得很不情愿。
我朝久哥抛出人权论,久哥看着我,像是头牛,他点燃根烟,故意把烟朝我这个方向吐说,我觉得这种问题你不该问我,我只是个生意人,你说我没人性,可是我还拿赚来的钱资助教育工程,我也知道做这种事违背人伦,倘若大家知道了,肯定会被道德谴责,还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背后还有千千万万的父母,是他们选择放弃,我只不过是执行,谁的罪更大?
我问他现在还做吗?
他指指腿说,不做了。
我继续想要追问,他说要是想问出现在是谁还在做屠小根本没门,行当有自己的规矩,自己脱离了行当是可以说,但这事儿说出去又有几个信,你要是去医院妇产科问医生,肯定会被保安赶出去,也别想着报警,警察不会给你立案。我说我之前做过协警。他哈哈大笑说,那你应该是个明白人。
开车从果子渠出来,我老感觉自己像是听了个魔幻现实主义故事,要不是当时我跟着大三儿亲眼见过,我也不信。
当时那得了肾衰竭的孩子被久哥送进冰柜,我也在现场,拦阻未遂,也没能敢揭发,其实我也算间接施害者。
久哥是个聪明的人,只是跟我聊经历,不跟我叙述细节,他们怎么运营,有多少人,如何打通上下关系,这些我一无所知,只知道去年那个放置冰柜的地点,八成早已搬迁。
在哀叹命运的同时,我想起久哥说自己两条粉碎性骨折的腿。那时候他开着车去省外办事,半道发生爆胎,再加上速度太快,车身就翻了,他从车里爬出来,朝爆掉的轮胎望,以为是辗了块尖石头。
仔细一瞧,是个破旧的洋娃娃。
满月酒当天,酒店里欢声笑语,我坐在宾客席上没动几筷子,小凡抱着孩子迎接着大家齐声喝彩的生日愉快歌,朋友发来短信说,久哥已经被缉拿归案,连日盘问下,又摘出几个联络人,昨天下午已将整个团伙一网打尽。
这时候,大三儿抱着自己的宝贝闺女迎了过来,冲着笑得灿烂的闺女说,这是你干爸爸,快跟你干爸爸拉拉手。
我轻轻地抓住孩子的小手,露出慈祥的微笑说,娃儿啊,你不知道吧,你其实还有一个姐姐!
大三儿匆忙地往后退,刻意让我松开手,他神情露出些许不自然,小凡喊他拍全家照,他像是猫一般迅速去往了台上,我看到小凡接过孩子,母爱泛滥般的欣喜,也许小凡对那事知情,或者一直被家人蒙在鼓里,但相机闪烁的瞬间,他们一大家子人笑得特别开心。
研究成果
“屠小”是历史遗留恶习,其所暴露的是社会残障儿童生存问题。据统计,中国每年有100-120万婴儿出生时带有缺陷,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残障儿童降生。残障儿童家庭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是原生家庭的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社会的排挤。
本文中的大三儿,面对降生的残障儿,选择了“屠小”来解决幼小的生命,从而“解放”整个家庭,这一选择,既可恨又可悲。
·END·
作者 | 田烨然
图片来源:千图网
(本故事系平台原创,纯属虚构,切勿深究)
惊人院好故事每日持续更新
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123@shiyan.com)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