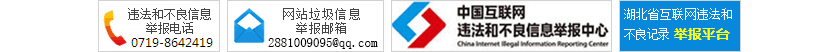|
|
晚上十点,萧楠拉上了55床和56床之间湖蓝色的隔断帘。
接着,他扫码拉开了床头柜下的陪护床,轻轻躺了上去。
一米八大个子的他蜷缩在窄窄的硬塑床上,无处安放的大长腿伸到了床外边。
静谧的夜里,“哐”的一声格外响亮。
“哥哥,怎么了?”病床上萧楠的爱人被惊醒了。
“吵醒你了?没事,睡吧。我不小心一伸腿踢到了柜门上。”他说得极是轻描淡写,就是不想让她多忧心。
“要不你来床上睡,我们一起睡得下。”
“我没事,你睡吧,明天还要手术呢,一起睡挤着你休息不好。”
随后,病房里静悄悄的,再也无话了。
只有这隔间內的两个年轻人,睁着眼出神地看进眼前的黑暗里,不知在思索什么。
清晨,五点四十,傅思思醒了。
她看了眼床下盖着睡袋的萧楠,蹑手蹑脚地下床了。
她轻轻摁亮了门廊灯,洗刷完后听见了楼道里滚动起的推车声。
是餐车来了。
“口罩事件”后,病区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措施,一日三餐都送到了病房外,傅思思本以为自己够早了,没想到前面已经排了七八人。
澄黄的小米粥配上四个素馅儿包子,再加上一份小菜,是傅思思给萧楠准备的早饭加午饭。
她的手术安排到了今天早上,自己是要空腹做术前准备的,就怕忙起来萧楠也没心思吃,这才早早就给他备下了。
早上七点半,萧楠目送傅思思步入手术室。
前两个小时萧楠还等的气定神闲,可是随着时间的拉长,他开始坐立难安。
十点钟的时候傅思思的堂姐、堂姐夫也来到了手术室外,几句心不在焉的寒暄后,萧楠的目光就紧盯着手术室的门口。
十一点,手术室的门开了,傅思思的主刀医生示意萧楠去谈话间。
此时的萧楠的心是恍恍惚惚的飘浮着,这一刻,他觉得自己一颗心沉重的厉害,孩子,老人只是轻忽的在他心头飘过,他好像只能想到这几日夜里的硬塑床。
“现在是这样,给你爱人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病变已经有所转移,而且位置很不好 ,和气管靠得很近,剥离干净很困难,有可能会损伤到喉返神经。”王主任说道。
萧楠听了王主任这话一时有些语无伦次,“王主任,不要紧,只要能清除得干净,我媳妇以后不能说话都行。”
“那怎么行,你爱人是当老师的,以后要是不能说话了,还怎么上班。”王主任反驳道。
“只要能保住命,王主任,你看着把不好的组织该切的都切了。”萧楠急切地说道。
王主任看萧楠这般说,一时有些语塞。
一直到下午两点,傅思思出了手术室,萧楠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才算落了地。
傅思思出院回家休息之后,她母亲有一回来看她,母亲虽然强撑坚强,傅思思还是看出她连日以来的憔悴。
傅思思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她问我疼不疼,是不是睡不好,吃得好不好……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口气。她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而我不想去看她的那双布满愁丝的眼神,因为心里太酸涩了。
母亲坎坷的命运使她不能再接受儿女出任何一点意外,她说,“你怎么命这么苦”。
这句话使我想到很多,于母亲而言,这是她无法诉说苦楚的一丝宣泄,她把这些归咎于命运。把自己无能为力,只能被迫接受的苦楚叫命运。
我听过有人说“苦树上结的是苦果子”,细究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不是命运的使然,而是对于苦难中的人来说,她想获得的在外人眼中的正常秩序的生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一个家庭的努力。要不然,几代人都是处在泥泞里。
我不爱听母亲“命太苦了”的话。要是认了,那就是太憨了,太怂了。
这场大病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这新的一代要活得更努力,更自在,即使生活中波折不断。
因为平平凡凡毫无波折的人太少太幸运了。既然不是那最幸运的一波,就更不能被生活打败。
我们这一代要坚韧,我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坚韧不拔地长大,即使生活中阻挠不断。
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123@shiyan.com)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