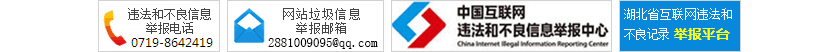|
|
《哈利·波特》活点地图,开启活点地图需要使用“我庄严宣誓我不干好事”这句咒语
泛90后作家大头马今年三十一岁,她声称自己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大量的时间用于打游戏,和一群朋友们玩在一起,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电竞选手。这群朋友会在凌晨两点的马路上把电动车并列开成一排,毕生信条是绝不工作。其中还有一个人想要拿菲尔兹天才数学奖(现在已经结婚,且没有拿到菲尔兹奖),正是这人,写了一篇与乔伊斯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著名篇章《阿拉比》同名的日记,其他人觉得这古怪的名字有趣,似乎意指着什么,又似乎只是一个奇怪的发音,这做法引得他们竞相模仿,写类似的同名小说。这段故事不仅被写进了书中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文,也可以视为这本名为《九故事》的小说集的创作概念的肇始。
这本书里遍布着她朋友们的身影,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到《乞力马扎罗的雪》,再到《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乍看之下性别和年龄均莫测的叙事者,以近乎无法无天的天真语气,在一种黄昏一样的色调中,在一个周杰伦的音乐也会变成古董的近未来里,诉说着关于自己友谊的伤感回忆。真实的生活和虚构的故事彼此交融,但是被压缩,更改面貌,变成了一些和世界名著同名的故事。至于为何要这样写,大头马说,“这样可以轻松地让你写下的内容在别人的眼里成为虚构的。”
她虚构了一个决意在台风“天鸽”侵袭澳门当天从蹦极台跳下以证明自我的疯狂女孩(《到灯塔去》),她思考的是先是被生活推动着创造出了虚构、继而虚构又搅入了生活的身为小说家的生活(《赫索格》),一个想要表明“我们不完全都想成为废物”的女孩的身影,在这本似乎被顽皮而聪明的诡辩话术充满的小说集中逐渐清晰了起来。
全书中唯一的中篇《白鲸》被放在篇首,这是大头马的最新创作,灵感来自于作者在警察局的实习经历。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由作者对这次实习经历的讲述,及其所开启的对于整本小说集创作来源的自述。这是一篇包含了很多有趣脚注的自述,我们或许无需把作者所说的全都当真,就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笑的故事,简约地一览大头马的独特性格和别样文风。而《九故事》这本实际上由六个故事组成的小说集,正是浸润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我庄严宣誓我不干好事
文/大头马
《九故事》是我的第四本书,收录了六个写于2016-2019年间的中短篇小说,按照完成的时间顺序分别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乞力马扎罗的雪》、《了不起的盖茨比》、《到灯塔去》、《赫索格》和《白鲸》。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有很多疑惑了,比如,为什么不干脆给这本书起名为《世界名著》?说真的我确实有考虑过。
赫尔佐格曾经说过,杀人不做计划,简直就是自杀。取名为《九故事》[1]已经足以让这本书迷失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叫《世界名著》只会让情况更加惨烈。鉴于我之前出版的小说均以极低的销量为出版社添了不少麻烦,出一次就得换一家,这本书我想稍作努力……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想先讲一条狗。这条狗叫马Sandy[2]。
严格来讲,马Sandy并不能算一只警犬。据我们所长说,泰迪是一种非常笨的狗,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警犬。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副驾驶,所长开着震天响的嘻哈乐,用的是华为手机功放——警车不配备车载音响。后面坐着两个摇摇欲睡的同事。
一小时前,我们连炸三个赌场失败,只能改去棋牌室碰运气,“看看可能遇到捞bzi[3]。”每个棋牌室都噤若寒蝉,人们礼貌而惊讶,只有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才能听到麻将推倒的声响。辖区内最后一间可能会有捞bzi的棋牌室大门已经锁上了,但二楼有房间亮着。所长一个眼神,大家心领神会。只有我穿便服,于是上前敲门。有人走过来,我隔着玻璃门比划,“还有没有房间?”门栓刚被卸下来,同事一闪现,只见一个身影迅疾地向二楼奔去,所长压低声音说,拦住她。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跑上楼梯,就听到一声大喝,“不许动!”所有人都吓得凝固在当场,我才发现这声音来自我本人。这一次,不是由棋牌室老板通过前台摄像头和传统声讯系统知会了所有客人有情况。我不好意思地冲大家笑笑,上了二楼。棋牌室小妹在身后用气声说,“捞bzi。”
电影《江湖儿女》
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这点,所长才极力打消我要把马Sandy放在所里饲养的念头。所长说,只有牧羊犬才能成为警犬。听了这话,我更加雄心万丈。我说,那么,我就要培养出世界上第一只警犬泰迪。所长伸出左手把手机音量调大,说,我最近喜欢听rap。
就在几天前,我刚来局里出现场的时候,所长还跟车里同事说,这是新来的小说家,是来体验生活的,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扫出激情,扫出风采。我才知道晚上的重大任务是扫黄。又过一天,马Sandy出现在所里大厅,连着三天我都没注意,以为是一块断了的拖把头。来报警的女孩蹲在地上逗它玩,我才发现那玩意儿会动。原来是一条狗。
至于我归根结底是怎么会碰到这条狗、它又怎么叫了这个名字、然后成为一条警犬的——
时间回退到十来年前。我和发小等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终日游荡在科大五教破坏天台大门,凌晨两点在大马路上把电动车开成一排占据机动车道,大量的时间用于打游戏,毕生信条是绝不工作。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职业电竞选手。前段时间我们抓了四个从哈尔滨自己买票坐飞机过来因为诈骗罪投案自首的大哥,他们曾经打《穿越火线》打到全国第八,当我问为什么不选择做游戏主播而是干这档子赔本买卖时,大哥的笑意苦涩中带着一丝骄傲。我懂。
我们不完全都想成为废物。其中一个想要拿菲尔兹奖的人某一天写了一篇日记,蛮有意思,题目叫《阿拉比》。这个怪诞的名字产生了某种魔力,引得我们竞相模仿。于是我也写了一篇《阿拉比》。后来这篇小说收录在讲述我们这群人是如何搞破坏的小说集里,并不引人注意。那本小说集叫《谋杀电视机》。再后来有影视公司买下版权想要改成影视剧,开过很多次会,大家都被一个关键问题卡住了:这些人为什么要砸电视机?
我们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电影《猜火车》
于是,这些事情又变成了另一篇小说,叫做《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当我发现“阿拉比”这个题目并非原创,而是来自乔伊斯时,我找到了一种轻松的解决如何让你写下的内容在别人眼中成为虚构的方法。第二个原因是我的懒惰令我不习惯为一项事物赋予名称。不仅是小说的题目,就连小说的人物……考虑到采用那些众人皆知的人名也许会招来偏见,因此我常借用朋友们的名字。在第二本小说集《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4]的最后一页,我向那些被借用名字到小说中的朋友们表达了感谢,为了不让此举给不幸在小说中认出名字的人以对号入座的猜测。
如此你会发现,起先是生活推动着你创造出了虚构,继而虚构又融入了生活现场,再次推动创造的齿轮滚动,现实与幻象就像一条首尾正反两面相连的莫比乌斯环,将你的全部世界卷入一个克莱因壶,你和你的世界的关系就像是光子与电磁波,你的世界是你在大尺度上的近似形象,以你的形式相互作用。你、世界、光子、能量、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协变量子场的表现形式。当我想到这些时,这些大脑中若有似无近于自指但模糊难辨的流动的存在又变成了另一篇小说,也就是这本书中的《赫索格》。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起初写小说的时候,我和所有年轻人一样缺乏读者。于是,我想了一个馊点子。把朋友们写进小说,“写朋友的故事,逼朋友不得不看”。这事儿就是这样,当你仅仅是借用朋友的大名时,你当然不会在乎他们是否看得到,因为你写的事情完全和他们无关。但是,当你开始把真实人物写入小说时,你就不得不开始考虑给他们起个化名。我一般习惯使用字母[5]。这在本书的多篇小说里得到了延续。
创造有无限种形式,我只是阴差阳错且无能的使用了最古老的方式之一。我从朋友们那里目睹了创造这一神赋人权更丰富的可能,比方说犯罪[6]。这些悄然发生的令人激动的创造促使我不得不以文字这样一种笨拙的方式将它们记录下来,也因此必须要隐去当事人的名姓、模糊事件发生的本来面目,防止人们从文本中提炼出有关现实的蛛丝马迹。这样就有了《乞力马扎罗的雪》。
到这里,将这些小说随机命名的理由似乎已经足够成立。不过,依旧存在其他的可能。譬如,有时候你不仅要隐去当事人的踪迹,也要考虑那些庞然有机体的自尊。在文学中,人们常使用隐喻。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不是为现在而写,是为未来。
我曾在另一个尚未收录在任何一本书中的短篇小说《全语言透镜》中讨论了一个猜想:为什么人们总是在使用一些循环反复的主题进行创造性的表达?这些主题是继承性质的、还是彼此独立产生的?假如我们能在文学中找到一座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否就能证实人类的艺术创造就如同索绪尔发现的语言学规律那样,是结构性的结果。按照这一猜想继续推测,我们将瞬间抵达事物的本质:人类的思想也具备这样的结构性。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时代,知晓这样的事情都将带来危险。因此,我谨慎地采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题目。这一谨慎在《到灯塔去》中得到了完全的变形和完全的释放,在小说《白鲸》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和完全的腰斩——
苏维埃宫概念图
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到马Sandy身上,讲一讲我是怎么遇到它的。几年前我与《白鲸》中案件的涉事人之一偶然相遇,得知了这个故事的源起,为了了解前因后果,一年后我进入警队实习,过程中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再后来,我又辗转颠簸换到另一个队,在一次值班时,见到了一条被主人遗弃被路人报警被同事捡回来的狗。狗的生命垂危,还剩下三条腿。第四天再没有人收养,它将被重新扔回街上。唯一的问题是,它不愿意走出去,而我们中没有一个想要做那个坏人。于是,我只好把它抱到外面,巴望它能有一点自知之明不再回来。就在那时,奇妙的命运再次降临,这条三天来没有哼过一声的狗说了一句,“阿拉比。”
“对不起你说什么?”
“阿拉比。”
“阿拉比?”
“阿拉比。”
“阿拉比是什么?”
“阿拉比。”
这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十来年前那位写下《阿拉比》的朋友。当然,他早已结婚,被剔除出了我们的队伍,也没有拿到菲尔兹奖。
于是我说,“要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你没有在一开始加入我们,就永远无法加入我们。”
“阿拉比[7]。”
至于马Sandy是如何成了一条警犬、又是如何破获了一起大案、最终又是如何——再一次——成为了虚构的一部分和将我卷入下一个现场的引子,这将是下一本书里我要说的故事。现在,假如你发现了这本书中某些故事的破绽,并拿着书来找我要个说法,我准备这样答复你,朋友,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电影《亚当斯一家》
[1]许多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一直认为美国作家J·D·塞林格将其1948-1953年间发表的九个短篇小说集结出版的书取名为《九故事》的原因来自公元前490-430年活跃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埃利亚的古希腊哲学家芝诺与其尊师埃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的一系列有关德谟克利特对于物质是否可以分割的谈话,后来这些谈话变成了若干悖论,其中有九则最为知名。但在塞林格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的回忆录中,她提到“事实压根没那么复杂”。
[2]此处由于不巧与某位我非常喜爱和敬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同名,就临时给它取了一个音译英文名。
[3]捞bzi,当地方言,意为傻子。
[4]你会发现随便给小说安上一个已经存在的题目的恶习在这本小说集里也得到了体现。现在回到正文中去。
[5]懒惰的又一次明证。并且,虽然在不同的小说中有时会反复出现同样的人物,但由于字母总是在书写的当下被随机选择,因此,同一个字母并不一定能代表同一个人。
[6]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但犯罪形式的创新在现实中更为精彩,譬如我们所长不久前破获的一起团伙盗窃案,两位犯人是在网络上相识并定下计划,然后在同一天到达本市,踩点、择机、作案、分赃,同吃同住十几天,然后各自离开。直到被抓捕归案前,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任何真实信息。
[7]那会儿我对狗还一窍不通。狗对人类却已经有了丰富的认识。当我送狗去做完手术,并准备以对狗过敏为由把狗甩给警队并向队长侧面索要报销费用时,队长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女儿对狗过敏”,第二句是“你会有福报的”。等狗出院的漫长日子里,我一再确认狗并不会说出复杂的声汇词,除了一种可能的情况:狗被附身了。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就在最近我查阅一篇意大利人类学家撰写的有关非裔巴西人的入巫、出神与着魔的民族志报告时,一开头就提到了一位Mineiro(奴隶)述及自己出生时发生的事情,“我从出生时就死了。那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当人们抬着他的尸体向坟墓走去时,坟冢边的狗突然开口了,它是这么说的:我死了一整夜。
大头马《九故事》
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123@shiyan.com)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