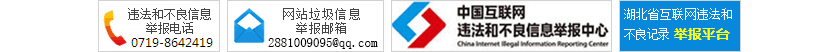|
|
本故事已由作者:碧仙,授权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发布,旗下关联账号“谈客”获得合法转授权发布,侵权必究。
1
三周前,亚安开始和一岁半的女儿珠珠一起吃饭。
三十岁的人,吞咽像酷刑,万分艰难,一小块肉,能卡半个钟头。
我轻轻走近他。
“要不要紧?”
亚安一额头的汗。
其实已经有十分疑心,这种怪样,不是一个压力过大可以搪塞的。
他的手在发抖,筷子在碗里滑,把碗边撞得铛铛响,终于叹气,对我道:“把珠珠抱走。”
我知道他终于肯说某些话了。
我和亚安成婚三年半,关系很好,大言不惭地讲,世上少此夫妻,女儿出生两个月已恢复夫妻生活,而且质量极高。
把珠珠丢给电视,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等他开口。
亚安放下筷子:“蔓,我患有某种肌肉退化病,三五年后,我的肉体会变成一颗木头,无药可医。”
我发愣:“你自己去医院看过了?”
亚安答道:“不。”
不得不说,有时候头脑运作过快是苦恼。
我仿佛挨一闷棍,定定注视他双眼:“你早知道自己罹患这种绝症。”
他垂头。
然后,又坚定地抬起头来,直视着我。
“我出生时已确诊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
我极惊讶,然后是悲哀,最后化为愤怒,复杂的情感,在胃囊里打转,要吐。
遗传病。
我站起来,两手发抖,支着桌子:
“珠珠是否有患病风险?”
他说:“是的。”
我没思考,拼尽全力,给他一耳光。
宁可他出轨,比不过今日的绝望。
他望着我,眼圈渐渐红了,掉下泪来:
“过去一年里,我始终和疾病抗争,服药,做理疗,肢体僵硬,头晕失眠,你毫不在意,到今天,连句关心都欠奉。”
我的嘴唇在发抖,我跌坐回椅子里,开始查询有关遗传性共济失调的信息。
亚安说:“不必问别人,没人比我知道得更多,患者大多数会在少年时期发病,从吞咽困难行动不便开始,三五年内,丧失全部行动能力。”
他刻意用语言刺痛我。
我不答话,不中他圈套。
他咬牙切齿地笑,把碗扫落地上,清脆一声,碎作一地晶莹:
“结婚之前,你本该看透的,自己愚蠢,怨不得旁人。”
2
我们降生在生育极度严苛时期。
养老艰难。
家庭呈倒金字塔状,所以知道亚安还有一个弟弟的时候,简直喜出望外。
到今天才明白,到底凭什么他特殊。
原来先天携带疾病,所以有生二胎权,他父母,果然爱子心切,哄着瞒着骗着,总算把这病人脱手,变成妻子责任。
我惨笑:“你还打算瞒我?你觉得能瞒到几时?孩子出生一年半,你发病一年多,你要怎么让我相信,不是处心积虑,拿孩子拴住我,叫我不得不管你?”
他嘲讽道:“你蠢我毒,不正是天生一对吗?”
我说:“我蠢也好,你毒也好,到底为什么珠珠要面临这样的厄运?”
他梗着脖子:“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做母亲的,一颗心揉碎,立刻把珠珠抱起,衣服都来不及换,下楼,开车,前往医院挂号。
结婚三年丈夫身体变差,我问清缘由后,连忙抱起女儿去医院
亚安无言跟上,在后座安抚珠珠的情绪。
到底是父亲,同我争口舌,不是真心。
到医院他默默去挂号。
我注视他背影。
才发现,这人走路已经开始变形,腿有点僵硬,弯不动,但,走到窗口,挂号,又找好电梯,才回头招呼我母女两个。
电梯里,我问:“什么科?”
他答:“神经外科。”
我忽然饮泣,抱紧珠珠,把脸埋在她稚嫩肩膀,亚安垂头,苍白道:
“她没有发病迹象,仍有机会。”
命运没有那样厚待我们。
做过CT、磁共振检查和二十二碳六烯酸测定,珠珠确定已遗传父亲家族疾病。
平均死亡年龄为三十五岁。
我一直哭。
珠珠被放到外婆家,不想让她知道生命的残酷真相,因此只有我同亚安来取报告。我看一眼,又看一眼。
亚安也流泪,我推搡他。
“鳄鱼的眼泪,少掉为妙。”
昔日的爱意全灰飞烟灭,一见面,唯一的愿望是用力掌掴他。
但不劳我动手,亚安已经连抽自己几掌,极用力,脸上立刻浮现青白指印,热辣辣变红。
他哽咽道:“我不知道——”
他抓住我,絮絮道:“假如我知道自己有病,死也不会拖累你跟珠珠,直到我发病,他们才对我说实话。”
我浑身骨头叫人抽去,顾不得身后只有地面,慢慢坐下:
“事到如今,说这些吗。”
3
医生对我们讲:
“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成熟的治疗方式的,家属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患者补充营养,延缓发病。”
我说:“我们不会放弃的。”
医生笑一笑:
“天下之大,可以多走一走,试一试,不是坏事。”
十分温柔讲道。
“但,也要根据家庭经济情况,不要太强求。”
是。
所有的医院都这么说。
我们已经花费了半年时间来确定这一点。
亚安即将失去劳动能力,从两个人养育一个孩子,变成一个人养育两个“孩子”。
一路上只剩沉默。
直到母亲家楼下,要接回珠珠的时候,亚安才说:
“你带孩子治吧,我放弃。”
我苦笑:
“放弃是零,零有什么用呢?我们需要加法。”
一笔钱。
一笔足够几年不工作,也能支持生活与医疗的钱。
我把眼睛看定了亚安,他叹气,按住我的手:
“给我时间想想办法。”
我温声说:“好。”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沟通。
次日凌晨一点三十七分,他在家中阳台坠亡,死的时候,穿蓝色条纹睡衣,一根烟掉在身边。
我听见嘭的一声。
四层楼,冲下去的时候,他还有极微弱的呼吸,我大哭,扑上去,抱住他的头,他的黑眼睛注视我片刻,鼻子里,嘴里,都流出血来。
我发不出一点声音,只是张着嘴嚎啕,眼泪汹涌,他长长吐出一口气,死在我的怀抱里。
警察和医生分开我们,我被拖着走,有女警为我披上一条毯子。
我颤抖着说:
“我家里还有孩子。”
她给我热糖水喝,安抚道:“我们会替你照顾。”
鉴定结论是,失足,因为露台栏杆锈蚀,成年人倚靠上去,立刻瓦解,他肢体失调,尤难自救,抽烟浇愁之际,跌落地面。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来看过六七次。
他同我打招呼:“姐。”
我不讲话。
“给孩子带了点东西,听说孩子病了,希望她早日康复。”
拦不住珠珠喜欢玩具,我只能挤出一点笑:
“费心。”
“听说大哥生前也是这个病,不好治吧?”
我腾一下站起来,眼睛里有火。
“如果你怀疑他死得蹊跷,可以向警方提出质疑,不必为了那笔赔偿金,一遍一遍,靠撕开别人的伤疤来套话。”
他讪讪道:“是是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冷笑:“贵方不是怀疑我故意杀人,打算来找点警方都没发现的证据,好把这个受益人送进监狱里去?”
他头上直冒汗:“您这话说的……”
忽然明白咬紧牙关是多么形象词语,成年人,遇到事情,拳头不能用,墙壁不能靠,只有一口牙,咬烂了,吞下去,无人知晓,保全面皮。
我说:“把你的东西拿走。”
他灰溜溜走掉。
我咬着牙只是笑。
说到底,是否他人都抱此怀疑?怀疑他为骗保自杀,怀疑我为骗保杀夫。
珠珠的小手按上我的脸。
“爸爸。”
她说。
“哪?”
“爸爸不在家。”
我哄骗她。
然后眼泪哗地流下来。
4
保险公司最后赔付一百九十六万。
这笔钱,我极强硬收入囊中,亚安父母心中有鬼,不敢争。
房子卖了,三百一十万,辞掉工作,忽然海阔天空起来。
人生三十年,从没想过,在短短一年内,终生忽然推翻,爱人过世,女儿患病,连根都失掉。
我带珠珠飞往国外。
飞机上,珠珠始终小声啜泣,我抱着她,心焦磨烂。
但,临座伸出援手。
他是个年轻男性,中国人,戴细黑金属框眼镜,把珠珠抱在膝头,并向我解释:
“飞机里气压不同,小孩子,耳朵会不舒服。”
果然按压几下,珠珠便云开雨霁,靠在他身上,极依恋样子。
忽然叫一声:“爸爸。”
我尴尬笑起来,忙抱她回来:“不好意思,小孩子不记人。”
他也笑:“孩子爸爸呢?”
我低头:“他几个月之前去世了。”
鬼使神差的,又添一句:
“孩子遗传了她爸爸的小脑共济失调,国内没有什么办法了,只好出来治。”
不知为什么,在飞机上向全然陌生的人吐露身世。
他露出恻隐神色,留给我一张名片。
“我是医生,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张青园。
他的名字。
我笑一笑。
这时候,人特别脆弱,我舌头紧紧压着牙齿,怕自己说话。一张口,一定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哀求。
做人最后一点体面,我还想留下,人家客气两句,切莫当真。
奈何对方不识趣,特别热心,沉吟片刻:
“我不是神经科的,但我朋友团队研究这方面内容,已经进行到临床试验阶段。”
我终于低头,忍不住追问他:“那——”
他已自觉建议:“落地以后,不妨保持联系,那边有什么进展,可以一试。”
我感激望他一眼。
人一点微妙的自尊,好像跌在泥坑里,还倔强举着一只手,只要它不沦陷,到底不算脏透了。
他也微笑起来。
但,又听见他说:
“如果我约会你,会出来吗?”
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凡事有所求才真实,第二只靴子落在地上。
我将珠珠抱起来,笑一笑:
“不合适。”
5
我在十分钟之前已经醒来。
但,嘘,不要出声。
因为珠珠也从睡梦中醒来,正在专注于探索我的眼睛嘴巴还有鼻孔,我还幻想着,装作熟睡,可以叫她无趣而退,再睡上个把小时。
幼儿的睡眠,是母亲的假期。
在她拉过床头的数据线塞进我耳朵里时,我的幻想终于破灭,我拦住她的手,叹了一口气,睁开眼睛。
她高兴地拍着手。
“妈妈,妈妈,充电。”
我也希望我靠充电就能获得无穷的精力。
真可惜。
我蓬头垢面地爬起来,问她:“饿了么?”
不用想也知道,不会乖乖吃饭。
他们具有一种奇妙的续航能力,不吃不喝,但大吵大叫。
我按下热水键,人又坐回床边发呆,两眼放空。
心里很乱。
事情已经过去半年,晚上还是会做梦,梦见亚安躺在水泥地上,濒死的眼睛紧紧盯着我。
水烧开了,我趿拉着拖鞋去找奶粉罐子,旧的喝完了,开一罐新的,量勺沉在奶粉下面,要找筷子去捞。
一转身就听见一声嘭。
奶粉罐子被女儿打翻了,现场像面粉厂大爆炸,一个小白人儿,坐在奶粉里,我浑身的力气都卸了,索性一头又扎到床上。
随便吧。
随便天怎么塌,不如学美国母亲,两片三明治,哄饱幼儿,然后逍遥自在。
我还是同张青园搭线,他为珠珠引荐了神经科的医生团队。
珠珠生命面前,泥坑打滚不值一提,哪怕是旱厕,我也不犹豫跳下去。
男人不会做亏本买卖。
他出人情,一定要你实打实还债。
有时候我跟他出去,有时候是珠珠治疗期间,我跟他走。
他有家庭。
但,不知为什么,不觉得委屈,也不觉得道德灼心,每一次,都好像斩断手足枷锁。
育儿,捕食,男女。
文明世界的矜持,礼貌,全都褪色,人家一勾,我就上手。
有时候珠珠错乱,叫他爸爸。
亚安知道一定痛心。
人一生就是父母子女,父母欺瞒,子女遗忘,不得不说可悲。
但张青园特别喜欢答应。
一听珠珠叫爸爸,满口答应,抱她到处去玩。
今日又是珠珠理疗日子。
把珠珠放在医院,在车上,他吻我脖颈,我痒得受不住,笑着推他,他手已经滑进我衣服里。
但做了亏心事的男人也特别听话,整好衣服,主动道:“我替你去接珠珠下来,你歇着吧。”
我百无聊赖缩在座位上刷手机,忽然看见手边一亮,他没带手机。
本来无资格查他手机。
但,屏幕内容太奇怪,我不得不注意起来。
他的妻子来信,问他:
“那女人,还没怀孕么?”
6
我疑心“那女人”是我。
张青园带着珠珠回来,我只得收敛目光,把珠珠抱了又抱,问她:“今天怎么样?”
她叽叽喳喳。
我余光打量张青园脸色。
他一解锁手机,忍不住就瞄我一眼。
我的心往下沉。
这一眼,自投罗网——他怕我看见过这条消息,那么,必然指我。
然后就发笑。
早知道张青园是二代移民,父母做一辈子洗衣店,供他读医科,处处急着同出身撇清关系。
没用。
没想到骨子里,还是节俭至极的人,老婆生不出孩子,连代孕钱都舍不得,要他出卖色相,同女人你侬我侬,骗一个婴儿回家,老爷太太视如己出。
我忽然说:“我要吃药。”
他强笑:“好端端吃什么药?”
我说:“现在吃还来得及,倘若真中招,我没法照顾珠珠。”
他小心翼翼:“伤身体的,不会那么巧吧,大家都不小了,万一有了,再说有了的事。”
我忽然发狂,撕打他,踢他:“你去不去?你去不去?”
到后面,嗓子都喊破,眼泪直流,珠珠吓哭了,也不敢出声,在安全座椅里抽噎。
我顾不上她,手脚发软,埋头大哭。
我不是个轻浮女人,可,丈夫过世不到一年,我已同人出双入对。
始终也有私心,异国他乡,我带着一个病孩子,我依恋这一点可靠,,刻意无视他不过是玩玩的现实。
到今天,温情脉脉面纱被撕破,才发觉背后算计,比贪色更不堪。
他被我打得脸色铁青,咬着牙。
“滚下去。”
他叫我滚。
我哈哈大笑。
我说:“张先生,人不能既要又要,要吃好处,又要脸,做出这种事来,挨一顿打,够轻了。”
他停车,扯开这边车门,粗暴把我扯出来,又把珠珠塞进我怀里,我踉跄两步,被沙尘填了一嘴。
我一只鞋掉在他车上。
珠珠大哭。
我抱紧她轻声哄:“好了好了好了……”
也不觉得痛,也不觉得冷,只是进屋时候,留下一串黑脚印,才想起来自己有一只光脚,到卫生间去洗,发现脚底磨起血泡,已经破了。
然后,我艰难走到马桶边上,一俯身,吐了。
7
本地是禁止堕胎的。
肚子里有没有生命,女人的直觉最准。
我吐完了,坐在椅子上,紧紧抱住自己膝盖,发抖。
一时软弱,可以造就无数麻烦。
他说他会离婚,他说他没有孩子,他说,他说,他说。
我举手抽了自己两记耳光。
我的眼泪流下来。
喃喃道:“亚安……”
我思念他。
春天的流感毫不留情袭击我这个脆弱人,我发高烧,说胡话,浑身发软,两天里,只是跟珠珠一起喝奶粉。
张青园好几日不问一句。
他相当撕裂。
不要脸的事做到底,但,给人揭破却不肯,又要起面子来。
邻居救我小命。
隔壁是一家教徒,电影里那种,一个胖胖的大妈妈,带着一群孩子。
他们有时候带苹果派来,也帮我带珠珠,是十分良善的一家人。
我迷迷糊糊的,感觉额头一凉,挣扎着看过去,珠珠正给人抱在怀里。
“谢谢……”
大妈妈埋怨:“病得这么厉害,怎么不告诉我?”
我烧得眼泪都干了,只能笑,拉住她一角衣摆。
“我好后悔。”
她一听在胸口画了个十字:“诚心诚意向主悔过,祂必将拯救你。”
是吗?
这世上还有东西可拯救我?
我身不由己跟她走。
病愈之后,我随她去教堂。
有罪的人,要忏悔,她带我到那间小黑屋,我坐进去,门关紧,隔着一扇小窗,我看见一双平静的眼睛。
他在等我说。
秘密像种子,种在心里就要疯长,直到枝叶都从你眼睛鼻子嘴巴里伸出来,你不得不把它吐出来,你死掉,它永恒沉默。
我感觉腔子里有火在烧。
它要出来了。
我说:“我和有妇之夫发生了关系,现在我想把这个孩子流掉。”
不是它。
火还在烧。
我忽然捂着脸大哭起来,然后用力攥紧了铁窗上小小的栏杆,眼睛可怕地瞪着。
我一字一顿说:
“我,杀死了我的丈夫。”
8
对受伤的人,要维持他的原状,及时就医,在专业人员来之前,不要搬运他,避免二次伤害。
报警的不是我,叫救护车的也不是我,是热心邻居。
我不得不摇晃他,加速他失血速度,以置他于死地,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恨,想说话,一张口,只能吐血。
我放下心来,大哭。
在带珠珠四处求医期间,我见到许多此类病患,大多数,已至晚期。
特别恐怖,比植物人恐怖,盖因植物人意识已不知所踪,共济失调患者各个清醒,一双眼珠,是唯一与外界通道,此外,浑身如木头。
没有一人幸运。
全部人用怜悯眼神看亚安,看他姿势古怪走来走去,挂号,缴费,开药,有大姐打量他几番,对我讲:
“二年半吧,最多了。”
我一下喘不上来气。
恨不得他是一块真木头,只要太阳晒晒,雨水浇浇,自己就能活。
要吃要喝,要拉尿,要放风,要关爱……
他已经不能抱珠珠,身体时常失去平衡,珠珠不懂,有时候拍着手笑:
“爸爸也摔跤。”
亚安的脸上露出极迷茫痛苦的神情。
那一夜辗转反侧,我走到客厅里。
亚安也在。
他沉默拿烟给我,沉默点燃,然后沉默相对吸烟。
都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终于他说:“珠珠给你,房子和钱都给你。”
我说:“你等死?”
他说:“事已至此。”
我说:“那你也应该知道,家里那一点钱,派不上什么用场。”
他说:“你再结婚生一个吧,等他大了,也能照顾珠珠,不然几十年之后,你也老了,伺候不了一个病孩子。”
我说:“假如你没骗我,没有孩子,我现在心甘情愿伺候你到死。”
一谈到这就要吵架。
我用力推过他。
阳台门大敞,他控制不住身体,跌跌撞撞,被我推得撞上露台栏杆。
栏杆一侧立刻崩断。
他脸上露出恐惧神情,伸手:“蔓——”
我走两步,又站住。
另一侧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他失去平衡就站不起来。
他的脸色变得惨白惨白。
千钧一发之际,我下定决心:
“对不起。”
他坠下去。
像一块石头。
他必须死,我需要钱。
哭,是真心的,爱,是真心的,奈何恨也一样真心。
我说完了。
9
我的英文并没好到听懂各种词汇的程度,只能微笑,也随大流在募捐篮里放了钱。
邻居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只是笑。
果然世上没有救世主,得到的唯一愉快,是不必再背负自己的秘密到死。
但眉头一皱,又要吐,忙不迭冲向卫生间,才想起小腹里的第二个秘密。
两个孩子,两个父亲,均非善类,我有时鄙夷自己有眼无珠,为世界延续恶劣基因。
我大可以驱车到临洲流产,摆脱厄运。或者,有大量机构,接收单亲妈妈,生育后,修养身体,可孤身走路,将婴儿留予慈善机构,统一抚育,待人收养。
不不不不不。
我立刻把第二种选择扫地出门。
何至于卑劣至此。
成年人头脑发昏,把后果全给婴儿承担。
我知道我还有其他办法。
从一个男人,走到另一个男人身边,这一次,连遮眼爱情都无,清清楚楚,投入深渊。
为什么中外婚礼服装都有面纱,盖头之流?结婚非要盲目不可。
我脸上浮现极悲哀的微笑。
但,手机已经解锁,手指已经按上张青园号码,我深吸一口气,矫饰出极温柔,极委婉声音。
“见一面好吗?有件好事想和你讲。”
一边讲,一边照镜子。
我已经开始有白头发了。
三十岁的女人。
眼泪滚下来,但笑容满面:
“是的,我很想你,离开你之后,我才知道到底爱你有多深,我不能离开你。”
珠珠不能离开你。
“最近我一直不太舒服,恶心想吐,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我就不会放你走。
“我不知道,我也很害怕,这个洲,堕胎是违法的吧?”
我会让我的孩子成为婚生子。
“不会,我们老家有句俗话,说带孩子,一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
丈夫,杀一个也是杀,杀两个也是杀。
我慢慢从卫生间走出来。
教堂的花窗投下彩色的,温暖的阳光,高高的十字架上,耶稣垂下悲哀的脸望着我。
一个心虚的我恐惧他的眼睛,不管在任意角度,总觉着他注视我,因为不需要眨眼,那永恒的,连绵的眼神,困住我。
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忽然对一座雕像讲话。
“别那么看着我!”
中文,极强横,周围人都侧目,但我恶狠狠瞪着祂,所以祂的眼神,也渐渐虚化了。
但我知我问心有愧。
可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满目疮痍……
我木木地笑了,闭上眼睛,不肯看,捂住耳朵,不肯听。
这一次,不能再输给男人。(原标题:《你瞒我瞒》)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
声明: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123@shiyan.com)删除! |
|